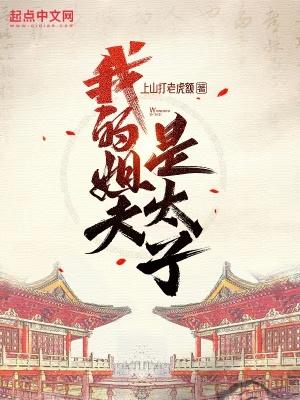秃鹫小说>铁血狼啸电视剧演员 > 第149章 新政之艰之三 巧破贪腐案(第1页)
第149章 新政之艰之三 巧破贪腐案(第1页)
朝堂之上,关于新政“理论危害”的论战仍在持续。那份来自江南、引经据典的奏疏,如同一颗投入湖面的巨石,激起了层层涟漪。支持新政的官员与质疑者引经据典,争论不休,双方皆旁征博引,一时间难分高下。这种看似高屋建瓴的争论,实则分散了朝堂的注意力,延缓了新政推进的效率,这正是反对者们所期望看到的。
然而,就在这看似僵持的关口,一桩看似不起眼的“小案子”,却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撕开了反对派道貌岸然的面具,为新政的推行赢得了至关重要的转机。
案件的突破口,依旧来自于那张无孔不入的“蛛网”。
这一日,老秦悄无声息地出现在御书房,向正在批阅奏章的萧绝和苏婉呈上了一份密报。
“陛下,娘娘,”老秦的声音低沉而平稳,“老奴手下的人在核查京畿地区试点州县的新税银入库账目时,发现一点微末异常。”
“讲。”萧绝放下朱笔。
“宛平、大兴等几个试点县,首批‘一条鞭法’折银上缴的税银,其成色、重量,与户部规定的‘官银’标准略有差异,虽极其细微,但多个州县同时出现,便显得有些不寻常。而且,这几个县的税银入库时间,也比预期晚了数日。”老秦禀报道,“老奴觉得蹊跷,便让下面的人多留了份心。”
苏婉闻言,立刻警觉起来:“细微差异?晚了数日?莫非是在熔铸、运输途中做了手脚?或是…”
老秦接过话头:“娘娘明鉴。老奴派人暗中查访了负责为这几个县熔铸税银的官炉以及押运的银车,发现并无问题。问题,可能出在入库之后,或者说…在账目之上。”
他取出一本看似普通的流水账册副本,指着上面几处看似合规的记载:“这是宛平县上报的税银入库清册。表面看,毫无破绽。但若与其邻县同期粮价、以及市面上私银兑换官银的贴水率进行比对…便会发现,他们折算农户粮棉为银两的‘基准价’,略低于市价。而这微小的差价,累积起来,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萧绝眼神一冷:“意思是,他们利用折银的环节,暗中压低了收购价,盘剥了百姓,然后将这笔多出来的银两…?”
“陛下圣明。”老秦躬身道,“老奴怀疑,这笔多出来的银两,并未入库,而是被层层截留了。但账面上,却做得天衣无缝,taxes总额与清丈后的田亩数完全对得上。”
“好一个‘天衣无缝’!”苏婉的声音带着寒意,“贪墨竟贪到了新政的头上,还做得如此隐蔽!若非蛛网心细如发,几乎被其蒙混过去!”
“能接触到核心账目、并有能力统筹此事的,绝非小吏。”萧绝冷声道,“查!给朕一查到底!朕倒要看看,是谁在朕的新政上蛀洞!”
“蛛网”与都察院的精锐力量立刻秘密行动起来。调查并未大张旗鼓,而是从外围入手,暗中监视户部负责接收、核算试点州县税银的几个关键小吏,以及宛平、大兴等县的主簿、钱粮师爷。
很快,一个可疑的线索浮出水面:宛平县那位因前县令被革职而新提拔上来的钱粮师爷,最近突然变得阔绰起来,不仅在京城悄悄购置了一处小宅,其家人更是添置了不少新衣首饰。
顺藤摸瓜,更多的蛛丝马迹被串联起来。几个州县的小吏之间,存在一些隐秘的金钱往来。最终,所有的线索都隐隐指向了户部清吏司的一位郎中——吴启明。此人官职不高,却是具体负责新政税收账目复核的关键人物,出身江南士族,与之前上那份“万言书”的御史大夫乃是同乡。
就在调查取得初步进展时,都察院一名派往宛平暗访的御史遭遇了“意外”,座骑受惊,险些坠马重伤。这更像是做贼心虚者的警告和灭口。
萧绝闻报,怒极反笑:“真是狗胆包天!看来,不动真格的是不行了!”
他与苏婉商议后,决定不再暗中调查,而是引蛇出洞,一击必杀!
苏婉亲自调阅了所有涉案州县的原始税粮征收记录、市场粮价记录以及最终的折银账册,利用她超强的计算能力和对数字的敏感,很快发现了更多做假账的痕迹。她并未打草惊蛇,而是将确凿的证据暗中交给了都察院心腹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