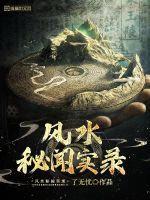秃鹫小说>魂穿曹操 > 第3章 暗格里的第一个盟约(第3页)
第3章 暗格里的第一个盟约(第3页)
他沉默了许久,最终没有发作,只是低声对贾充下令:“陛下近日忧思过重,夜读《春秋》至‘弑君’条目,恐伤神明。不如暂以志怪之书怡情养性,待龙体康健,再研经义不迟。”
第二日,曹髦发现自己书架上的《春秋》、《尚书》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山海经》、《搜神记》之类的读物。
书页崭新,散发着油墨与浆糊的气味,与他记忆中那些泛黄卷边的典籍截然不同,那气味刺鼻,像是对过往的嘲弄。
他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心中默念:你们换得了书,却换不了我脑子里己经装下的东西。
他不再执着于书本,转而给了李昭一个新的任务。
他让李昭留意宫人们的闲谈,特别是那些从司马府传出来的只言片语,无论多么琐碎,都要记下。
很快,一份份关于“司马府内宅几位夫人争权”、“大将军司马师与幼弟司马昭面和心不和”、“司马昭之妻王元姬屡与夫婿不睦”的传闻,便被整理出来,成了他案头新的情报。
纸页上墨迹浓淡不一,有的字迹潦草,像是仓促记下,却字字如针,刺入曹魏权力核心的缝隙。
五日后,王肃借着入宫为皇帝讲经的机会,将一方色泽古朴的玉佩悄然夹入所携经卷之中。
经书呈上时,他低首退步,袍袖轻拂案角,不动声色。
待他离去,曹髦缓缓展开卷册,玉佩滑落掌心——入手温润,仿佛蕴藏着地脉的暖意,正面用篆体雕刻着一个清晰的“魏”字,背面则是两个小字——守节。
玉面微光流转,像是月光浸染过的寒泉,触手生温,却又透着一股沉静的凉意。
这己是无需言语的确认,也是沉甸甸的托付。
那一夜,曹髦没有用墨。
他取出一管以紫草与胆矾调制的隐墨,在素帛上写下八字。
初时无痕,待火烤方显血红——如血,却非血。
“风起青萍,共执斧柯。”
他默念:“墨可洗,字可隐,唯此心不可掩。”
血书之险,他深知;然誓言若不能渗入骨髓,又何以动天地?
他将素帛小心藏入一本《礼记》的夹层中,交给了李昭。
当李昭带着那卷书离开时,曹髦知道,他与王肃之间,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盟约,己经无声地缔结。
又一场暴雨不期而至,豆大的雨点砸在太极殿的琉璃瓦上,发出沉闷的声响,仿佛千军万马在奔腾。
雨丝被风卷着,扑打在廊柱上,溅起细碎的水雾,湿冷地贴上他的脸颊与衣襟,布料紧贴脊背,寒意渗入骨髓。
曹髦没有掌灯,只身立于殿前廊下,任凭夹杂着水汽的冷风吹拂着他的衣袍。
他望着宫墙之外,司马府邸方向那片被雨幕模糊的灯火,手中紧紧握着那枚刻有“魏”字的玉佩。
玉石的冰凉触感,让他愈发清醒。
他不再是被动等待审判的囚徒,不再是史书上那个被一笔带过的悲剧符号。
他己经迈出了第一步,从被书写的历史,走向了那个书写历史的人。
远处,一道闪电划破天际,紧接着是一声沉闷的雷鸣滚过,犹如命运擂响的战鼓。
他迎着风雨,对着那片象征着无上权力的府邸,用只有自己能听见的声音,轻声说道:“司马师,你以为我在演戏……可你不知道,这场戏,是我写的剧本。”
雷声渐渐远去,暴雨的喧嚣也随之减弱,化作连绵不绝的淅沥雨声。
天地间仿佛只剩下这单调的声响,洗刷着宫殿的每一个角落。
就在这万籁俱寂的刹那,一缕箫音自东厢悄然浮起,如雾穿廊,似梦非梦。
是洞箫。
吹的竟是先帝驾崩那夜宫中禁奏的《思君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