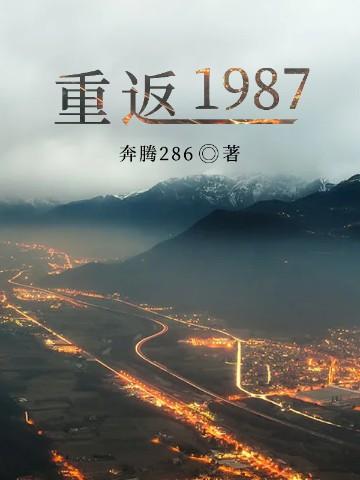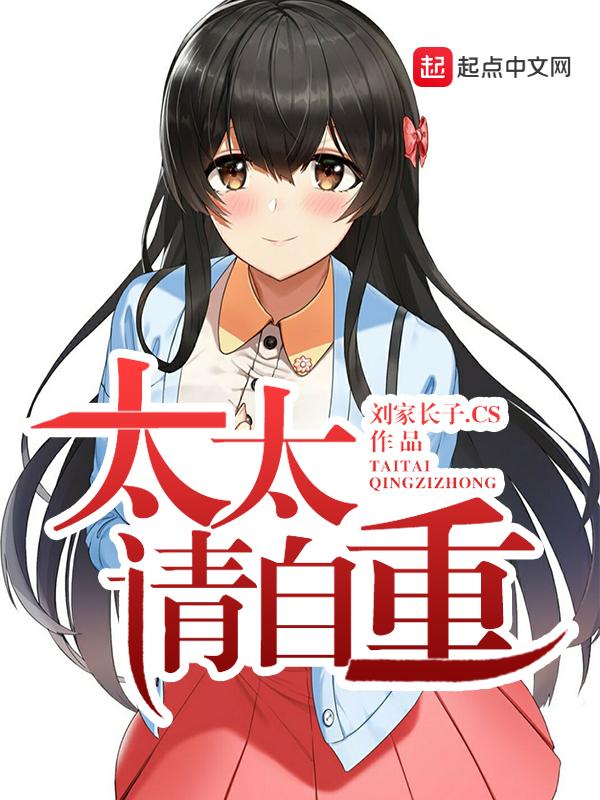秃鹫小说>万剑朝宗最新章节目录 > 第三百七十四章 摩天宴上(第3页)
第三百七十四章 摩天宴上(第3页)
全球成立了“记忆共治联盟”,各国设立“真相调解院”,以共忆证据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曾经因族群冲突世代为敌的两族,在共享了彼此祖辈受害经历后,共同修建了一座“双生纪念馆”,馆内陈列的不是胜利者的荣耀,而是双方失去的孩子们的玩具与日记。
艺术领域掀起革命。音乐家创作出“情绪协奏曲”,能同时表达喜悦与悲伤;画家用记忆投影技术绘制“多维肖像”,展现一个人在不同人生选择下的命运分支;甚至文学也开始变革,《虚构小说》被重新定义为“可能性探索”,读者可通过冥想体验书中角色的真实情感波动。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拥抱这场变革。
西部荒原上,出现了一支名为“静默之子”的团体。他们割断舌头,焚毁家谱,宣称“纯粹的空白才是灵魂的净土”。更有极端分子袭击记忆存储中心,试图炸毁保存前世记忆的主晶库。
面对暴力,念安始终坚持非对抗原则。“他们不是敌人。”她在一次演讲中说,“他们是恐惧的化身。恐惧记忆带来的责任,恐惧真相撕裂现有生活,恐惧一旦开始回忆,就再也找不到原来的自己。”
她提议建立“缓冲村落”,为不愿立即接入共忆网络的人提供过渡空间。在那里,人们可以慢慢接触轻微强度的记忆片段,学习如何承载而不崩溃。三年内,超过六十万人自愿走出村落,主动登记成为“记忆公民”。
与此同时,科学家发现了一个惊人现象:随着跨世记忆的普及,人类大脑正在发生缓慢进化。部分新生儿展现出“先天共感能力”,能在他人情绪波动时产生同步生理反应;更有极少数儿童声称“一直记得”自己前世的职业与亲人。
医学界为此展开研究,最终得出结论:这不是幻觉,而是潜意识层面对集体记忆的自然调取。这意味着??人类正逐步摆脱“个体孤立”的认知模式,迈向一种全新的“群体意识共生态”。
而在这一切背后,那枚来自陆知远的晶核被嵌入启明洲地基,成为新文明的精神锚点。每逢月圆之夜,它都会释放一圈柔和波纹,覆盖全球,提醒所有人:
**你不必独自承受一切。**
五年后的春天,念安收到一封匿名信。信纸是普通的再生木浆纸,字迹稚嫩,像是孩子所写:
>“阿姨,我昨天梦见了一个穿蓝衣服的叔叔。他对我笑,说他是我的曾祖父。他还说,谢谢我现在还能叫出他的名字。我没见过他,但我哭了。妈妈说,这是因为我的心早就认识他了。”
>
>“我也想把我的梦写进《共忆录》,可以吗?”
附件是一幅蜡笔画:两个人影手拉着手,站在开满野花的山坡上,头顶飞着一群发光的蝴蝶。
念安将画贴在办公室墙上,旁边写着一行小字:
**记忆的终点,从来不是答案,而是更多的问题。而提问本身,就是觉醒的开始。**
某日黄昏,她独自登上归忆岛旧址的灯塔。海浪拍岸,潮声如诉。她取出父亲留下的最后一块晶片,投入海中。晶片沉入海底瞬间,整片海域泛起幽蓝涟漪,似有无数低语在回应。
她知道,那不是结束。
黯语者或许永远不会彻底消亡,因为它根植于人性深处对痛苦的逃避本能。但只要还有人愿意开口,还有人愿意倾听,还有人能在泪水中依然选择相信,光明就永远有反击之力。
夜幕降临,第九门悄然变幻形状。
这一次,它成了一本书的模样,封面空白,等待书写。
念安转身离去,脚步坚定。
风起了,吹动她的长袍,也吹散了岸边最后一缕暮色。
而在世界的另一端,那个曾在述魂节说出真相的痴呆老人,正抱着孙女坐在院中。
小女孩仰头问:“爷爷,人死了以后,还会回来吗?”
老人抚摸着她的头发,轻声答:“会啊。只要还有人记得,他们就会住在别人的心里,活得比从前更清楚。”
小女孩点点头,忽然笑了:“那我以后也要做一个让人记得的人。”
星光洒落,万籁俱寂。
在这颗蓝色星球的某个角落,又有一个灵魂,轻轻说出了那句话:
**我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