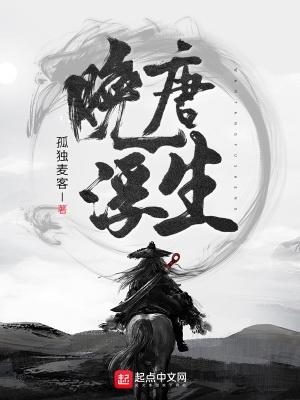秃鹫小说>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mobi > 第59章(第2页)
第59章(第2页)
陈崇对王莽的称呼,说明摄皇帝可以被称为“陛下”。这封信透露了王莽受命的意义:居摄元年王莽祭天,昭示天命已经转移到他身上。从此王莽就能够和天命互动感应了。他思考,能影响天地之气;他说话,能改变天地物理;他施政,能实现王化。所以,陈崇把王莽讨翟义的诏书出炉的时间和翟义叛乱被镇压的时间一对比,“神奇地”发现,王莽还在构思诏书时,翟义已经露出败象;诏书写好之日,正是翟义兵败之时;收到诏书的时候,翟义就被杀了。
所以,平叛这件事压根不是我等官兵之力,而是陛下一个人的功劳!翟义之乱并不见得是坏事,而是王莽能够和上天同呼吸共命运的祥瑞啊!
陈崇受宠不是没有原因的,从早期为王莽设计上位“路线图”,到说出这样一番天人感应的肺腑之言,谁心里不美滋滋的。
不久,陈崇和将士们凯旋长安,围观的市民可能不知道,这将是他们最后一次目睹汉军的胜利归来。
王莽在未央宫白虎殿置酒劳军2,将士们欢饮庆贺,期待着朝廷的褒赏。
陈崇是监军,了解战事经过,就被要求考定军功,以便行赏。论功行赏本属常事,不过这次不太一样。王莽借此事正式推行了“五等爵制”,也就是公侯伯子男的爵制。
在王莽等人看来,汉朝延续秦朝施行的二十等爵制以及诸侯王制都是不合乎礼的,作为儒家改制的一部分,应该取消3,改为周朝的五等爵制4。
其实周代爵制十分复杂,但当时王莽和他的一些儒学顾问认为周朝施行的是五等爵制。早在汉成帝时期,汉廷就已经封殷(孔子)、周的后裔为公,所以仿照周朝进行爵制改革是朝野共识,王莽只是继续推行而已。这些将士们功高的封为侯、伯,次等的封为子、男,而不再称列侯,二十等爵制里的关内侯也改称“附城”,取附庸之意。
五等爵制的实施,意外惹出一个问题:王莽的宗法身份。
王莽是摄皇帝、假皇帝,那么他原来的新都侯爵位如何处理?安汉公的公国又该怎么安排?
安汉公是尊称,与摄皇帝倒不妨碍,就好比周公称“假王”,也仍然是“公”。新都侯的爵位就不同了,这是王莽从父亲王曼手中继承的,意味着王莽是新都侯国社稷的继承者。但他现在又是汉家社稷的看护者,一个人同时为两种规格、两个姓氏的两个社稷行使宗法权,很怪异也很别扭。
况且,五等爵制的施行,让王莽的两个儿子都从原来的列侯进位成了公爵,侄子王光也被封为侯爵。王莽怎么还能当新都侯爵呢?
幸好有周公的先例!周公封鲁,长子伯禽到鲁国当国君。鲁国是侯国,但不妨碍周公的身份。
所以,王莽把长孙搬了出来,就是在吕宽大案里死于非命的王宇和吕焉之子王宗,继承新都侯爵位。这就意味着,王莽退出了新都侯国的宗法义务,让王宗成为王曼这一支的继承人。王莽的儿子则是自己宗法上的继承人。
这个问题刚应付过去,王莽的母亲又去世了。老问题再次被提出来:王莽怎么为母亲服丧?
服制是丧礼最重要的部分。在儒家看来,人与人之间不存在博爱,而是等差之爱,一个人如果自称爱父母和爱陌生人等同,那一定不是发自内心的爱,是虚伪,甚至是“禽兽”5。正常人会更爱与自己亲缘更近的人。所以,服制的不同是基于人之本性的流露,关系越近,爱得越多,哀伤也就越重,在服制上也就各有等差。
父母去世,乃人事之至哀,孝子要服最重的丧服,这本没有什么疑问。但班固在这里给了王莽一个看似平常、实则极为致命的描述:
(王莽)意不在哀,令太后诏议其服。6
说王莽的心思不在表达哀痛,而是忙于令群臣讨论他服丧的服制。
儒家丧服礼仪俱在,难道说为父母服丧的服制还需要讨论吗?
对王莽来说,需要!就像他刚刚把新都侯的爵位让给了长孙,说明他在宗法上不把自己当作王曼的儿子,所以也不能像普通人那样给母亲服丧。
当然,这与王莽是否真的悲伤是两回事。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外人未必深知。阮籍母亲去世,在人前他依旧喝酒吃肉,以致被闲人向皇帝“举报”为不孝,可他在无人之处悲痛呕血,难以自持。所以,班固说王莽“意不在哀”,未可全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