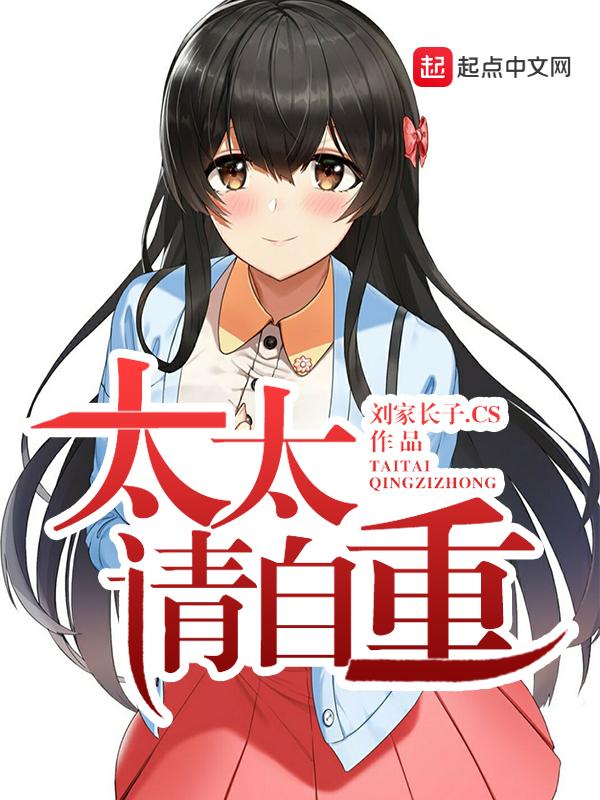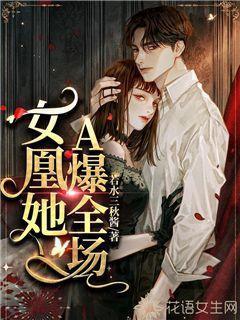秃鹫小说>重生四合院捡漏 > 第22章 手抄笔记的魅力(第1页)
第22章 手抄笔记的魅力(第1页)
门缝下的纸条还在桌上,我盯著那行字看了两秒,顺手塞进工具包夹层。天刚亮,外头有扫地的声音,沙沙的,节奏很稳。我起身把显微镜收进抽屉,又从最里层摸出个用牛皮纸包好的本子——《基础物理笔记》,边角已经磨毛了,纸页泛黄,是我穿越后头三个月手写的。
正翻著,院门口传来脚步声,不快,但每一步都踩得实。抬头看见娄晓娥站在门槛外,手里捧著个布包,没敲门,只朝我点点头。
“还你东西。”她走近,把布包放桌上,打开,正是那本笔记。
我愣了下:“你什么时候拿走的?”
“前天。”她说,“你送显微镜去厂里那天,趁你不在,跟秦京茹借的。”
我皱眉:“她不该给。”
“她问了我三次,要不要借。”娄晓娥看著我,“我说,我想看看你脑子里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没说话,翻开本子。封面换了新牛皮纸,边角压得平整,里头每一页都用铅笔做了批註,问题写在空白处,密密麻麻。有一页讲热胀冷缩实验,我用蜡烛加热铁钉,记录伸长量。她在旁边写:“若用煤炉余热做持续加热,是否可测更小形变?”
另一页是槓桿原理推导,我画了个挑水扁担的示意图,標了支点和力臂。她写:“若以此法测材料应力,是否可用於染料罐壁厚检验?”
我翻得越来越慢。
“你全看了?”
“通宵看完的。”她说,“昨天白天也看了。一共三遍。”
我抬头:“看懂了?”
“不是全懂。”她指了指中间几页,“这部分关於金属疲劳的推论,你用铁丝反覆弯折做实验,记录断裂次数和角度,再反推材料极限。这方法……太土了,可逻辑是对的。”
我笑了下:“土才好用。没设备的时候,就得靠手边的东西。”
“可你不是有知识吗?”她问,“为什么不用书上的標准方法?”
“书上的方法要仪器。”我说,“我们厂里连游標卡尺都轮流用,更別说测力计了。我能做的,是让人用铁丝、蜡烛、秤砣,也能得出接近的数据。”
她点点头,忽然问:“你写这些,是给谁看的?”
“没人。”我说,“最开始是怕忘了。后来……写著写著,就成习惯了。”
“可它能帮人。”她语气认真,“我爹看过你修工具机的记录,说你写的热处理流程,比厂里老师傅传的还准。但他不信你能写出来。”
“他信不信不重要。”我说,“数据对就行。”
她没接话,从兜里掏出一张纸,递给我:“我整理了几个问题,有些是我不懂的,有些……是我觉得你能解决的。”
我接过一看,上面列了七八条,全是基於笔记內容的延伸。最后一条写著:“若知识也能像工具一样交换,是否该有个『等价標准?”
我抬头:“你这是要开课?”
“想跟你学。”她说,“不是背公式,是学你怎么想。”
我沉默了一会儿。以前在现代,实验室里大家各忙各的,討论也只在项目节点。没人会捧著我的笔记通宵看,更没人问“你怎么想”。
“晚上?”我问。
“七点,老地方。”她顿了顿,“这次不用躲了。问题太多,站著说不完。”
我点头,把笔记重新包好,放进工具包最里层,动作很轻,像收图纸那样。
她看著我:“你觉得我……是在玩?”
“不知道。”我说,“但你写的这些问题,不是隨便看看就能问出来的。”
她嘴角动了动,没笑,但眼神鬆了些。
正要走,傻柱从外头晃进来,手里拎著饭盒,路过门口瞅了一眼。
“哟,”他站住,“这破本子比粮票还金贵?娄小姐亲自送回来?”
娄晓娥没理他。
我也没说话,只把工具包拉链拉上,扣好。
傻柱咧嘴:“林风,你这记的啥?『牛顿三大酷刑?”
“力学基础。”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