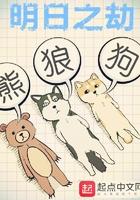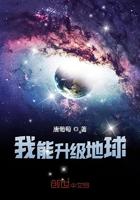秃鹫小说>去父留子N年后被发现了玄尧 > 5060(第4页)
5060(第4页)
桌上已经摆好了三副精致的餐具,银器熠熠生辉,瓷盘洁白无瑕。中间的花瓶里插着今早刚从街角花店买来的新鲜郁金香,每一朵都姿态优雅。一切都无可指摘,像一幅精心构图的静物画,充满了物质带来的丰裕与巴黎左岸特有的文艺安宁。
但,太安静了。
除了厨房里隐约传来的炖汤的细微咕嘟声,偌大的别墅里缺乏一种真正的“生活”的噪音——没有随意的谈笑,没有父母为小事斗嘴的烟火气。
这种安静,并非宁静祥和,而是一种被高标准的审美和秩序规训过的、略带压抑的真空。
终于,温父还是出现在了餐桌旁,赶在了汤被端上之前。
他穿着沾了些许群青色颜料的亚麻衬衫,头发有些微乱,眼神里还带着一种从创作激情中抽离出来的恍惚。
“哦,Lucas回来了。”
温父对着儿子点了点头,嘴角牵起一个微笑,但焦点似乎并不完全在此处。
晚餐开始了。
“这次去亚洲分部,情况怎么样?”
温母舀了一勺蔬菜汤,动作优雅,开启话题的方式如同主持一场商业会议的开场白。
直接、高效。
“还不错。新的供应链渠道基本打通了,就是文化差异需要慢慢适应。”
温晏明回答得条理清晰,如同在做汇报。
“嗯,适应成本必须计算在内。任何时候,效率和成本控制都是核心。”
温母微微颔首,给出指导意见,随即话锋一转:“对了,我上周和蓬皮杜中心的策展人吃饭,他们明年有个不错的项目,我觉得可以以家族基金的名义赞助一下,对于提升我们的品牌形象和文化地位很有帮助。Lucas,你跟进一下?”
她的话是对着儿子说的,但眼角余光似乎扫了一眼旁边的丈夫。
艺术,是唯一能同时引起她和丈夫注意的话题,尽管出发点截然不同——
对她而言,是投资、是声望、是社交资本;对丈夫而言,是纯粹的精神乌托邦。
温父果然被这个话题吸引,从恍惚中回过神:“蓬皮杜?是哪个方向的展览?如果是那些过于概念化的装置艺术,我认为并没有赞助的必要,那是对艺术精神的稀释。”
他语气里带着艺术家特有的清高与挑剔。
“是一位具象派大师的回顾展,笔触和情感都极其充沛,符合你的品味。”
温母应对自如,仿佛早就料到丈夫会有此一问。
“相关资料我让助理明天发给你看看。”
她成功地将丈夫拉入了谈话,但对话立刻滑向了关于艺术纯粹性与当代性的轻微辩论——一场永远不会有什么结果,但足以填充餐桌时间的、高水平的各说各话。
温晏明安静地吃着盘中的煎鸭胸,火候完美,酱汁浓郁。
他偶尔插入一两句,或是赞同母亲的观点,或是理解父亲的坚持,扮演着那个完美的、弥合分歧的儿子。
脸上的笑容依旧温和,语气依旧不疾不徐。
但握着刀叉的手指,关节微微有些发白。
温晏明看着父母。
他们交谈着,用词得体,逻辑严密,甚至偶尔会因为某个共同认可的艺术观点而相视一笑,看起来如此和谐、登对,是一对令人艳羡的、拥有极高智慧和品味的眷侣。
然而,他比谁都清楚,这光滑表象下的裂痕。
母亲永远不会真正理解,父亲为何能为一抹理想的蓝色而废寝忘食,视画廊的盈亏为无物;父亲也永远无法共情,母亲在谈判桌上纵横捭阖、为家族财富添砖加瓦时所获得的巨大成就感。
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坐在同一张餐桌旁,却仿佛隔着厚厚的、隔音的玻璃墙。
他们能看见对方的嘴在动,能听到对方的声音,但那些话语背后的情感核心、那些驱动彼此行为的根本动力,却从未真正传递过去。
他们尊重彼此的领域,偶尔合作,维持着体面,甚至因为有了他这个“作品”而拥有了共同的目标——为他创造一个“完美”的家庭环境。
但这其中,缺乏最本质的东西:试图穿透玻璃墙,去触碰对方内心世界的、笨拙却真诚的努力。
温晏明放下餐巾,微笑着说:“我吃好了,你们慢用。父亲,母亲,这次给你们带了点礼物,放在客厅了。”
“谢谢,我的儿子。你总是这么细心。”
温母报以赞许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