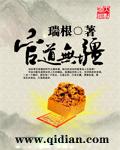秃鹫小说>秦国名将王翦下场 > 第61章 陇西伏波临洮烽燧 这狼烟倒着飘(第2页)
第61章 陇西伏波临洮烽燧 这狼烟倒着飘(第2页)
“准备突袭!”王翦拔出昆吾剑,用手势示意左右。三名亲兵同时发力踹开木门,火把瞬间照亮了烽燧内部的景象。
眼前的景象让久经沙场的王翦都惊呆了:烽燧下层被改造成了一个复杂的机械室,十几个匈奴士兵正在操作着一套奇特的装置——巨大的铜制风箱连接着陶土管道,管道末端通向烽燧顶部的灶膛;旁边堆放着装满马矢和油脂的陶罐;墙上挂着几张兽皮绘制的图纸,上面画着烽燧的结构图和信号编码表。
“杀!”李敢大喝一声,率先冲了上去。匈奴士兵猝不及防,瞬间被砍倒数人。但剩下的人反应极快,纷纷抄起弯刀抵抗,同时有人试图破坏装置。
王翦一眼就看到了装置的核心——一个嵌在墙壁里的青铜阀门,连接着通向外部的管道。他飞身过去一脚踹开试图关闭阀门的匈奴士兵,昆吾剑顺势斩下,将阀门的操作杆钉在墙上。
“别碰那个风箱!”王翦大喊。他注意到风箱旁边的陶罐上贴着楚地的朱砂符咒,与石棺坪发现的镇墓兽符咒如出一辙。这证明匈奴的技术支持确实来自楚地反秦势力。
战斗很快结束,八名匈奴士兵被斩杀,两名被俘虏。王翦立刻检查那套装置,发现其原理并不复杂:通过风箱强制鼓风,将灶膛产生的烟雾通过特制管道从烽燧背面送出,利用山坡的地形和夜间的局部气流,造成狼烟逆流的假象。马矢和油脂的混合物则能产生更浓重持久的黑烟,增加迷惑效果。
“将军,这是从俘虏身上搜到的。”亲兵呈上一个羊皮袋,里面装着几张竹简,上面用秦隶写着各烽燧的信号编码,甚至标注了每个烽燧燧长的姓名和性格弱点。
“楚人果然在背后策划这一切。”王翦捏紧竹简,指节发白,“他们不仅提供技术,还摸清了我们的布防和人员情况。”
他走到被俘虏的匈奴士兵面前,用匈奴语问道:“是谁教你们这套装置的?那些图纸从哪里来的?”
俘虏惊恐地看着他,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王翦示意亲兵松绑,递给他一块干粮:“说出来,我饶你不死。”
俘虏狼吞虎咽地吃完干粮,终于开口:“是……是戴着青铜面具的黑衣人。他们说只要按他们的计划扰乱秦人的烽火,就能得到十倍的盐和铁。他们还说,这只是第一步,等你们的防线乱了,真正的大军就会从洮河冰面进攻。”
“黑衣人有什么特征?”李敢追问。
“他们说话像南边来的,”俘虏回忆道,“为首的人手指少了一截,腰间挂着龙形玉佩,他看图纸时总说‘这是黄石公所授秘法’。”
王翦心头一震。黄石公?这个名字似乎在哪里听过。他突然想起石棺坪出土的竹简中提到过“圯上老人”,难道就是此人?
就在这时,一名士兵在烽燧上层的灶膛里有了新发现:“将军,这里有个暗格!”
王翦立刻登上上层。灶膛内侧果然有一块松动的石板,移开后露出一个青铜匣子。打开匣子,里面没有金银财宝,只有一卷用丝绸包裹的竹简和半块断裂的玉符。
竹简展开后,上面的内容让王翦呼吸一滞——开篇赫然写着“太公兵法卷一”几个大字!字体是典型的楚隶,但笔锋刚劲有力,绝非普通术士所能写出。
“是《太公兵法》!”李敢失声惊呼,“传说中黄石公授予智者的兵书!”
王翦小心翼翼地翻阅竹简,发现里面不仅有兵法原文,还有许多朱笔批注,详细解释各种战术的运用。批注者显然对秦军的布防了如指掌,甚至在“火攻篇”旁特别注明了临洮长城烽燧的弱点:“积薪虽足,然分布过密,一炬可连营。”
“将军,您看这里!”李敢指着最后一卷竹简的空白处。那里有几行小字,不是批注兵法,而是一句预言:“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五星聚东井,刘季当王。”
“刘季?”王翦皱起眉头,这个名字从未在军报中出现过,“是哪个部族的首领?”
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但王翦知道,这个名字绝非凡品。他将竹简小心收好,目光投向窗外混乱的烽火信号,心中突然涌起一股强烈的不安。
匈奴的干扰只是表象,楚人的阴谋也只是冰山一角。从周鼎残足到逆风狼烟,从昆吾剑到《太公兵法》,一张跨越数百年的大网正在缓缓收紧,而那个名叫“刘季”的人,或许就是这张网的最终目标。
【三:玉符玄机】
天色微明时,王翦己经带着青铜匣子回到了临洮长城的中军大帐。帐内暖意融融,与外面的冰天雪地判若两个世界,但这丝毫无法驱散王翦心中的寒意。
“将军,各烽燧的混乱信号己经平息。”李敢进来禀报,脸上带着疲惫却兴奋的神色,“我们按您的命令,让所有烽燧改用‘首上烽’——只举火不举烟,并且每刻更换一次频率。匈奴人的假信号立刻就暴露了。”
所谓“首上烽”,是秦代烽燧的应急编码方式,指烽火升举的速度和高度异于常规,用于在信号系统可能扰时传递真实信息。这种临时变更的编码方式,只有秦军高级将领知晓,果然让匈奴的干扰失去了作用。
王翦点点头,示意李敢坐下:“说说审讯结果。那两个匈奴俘虏还有什么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