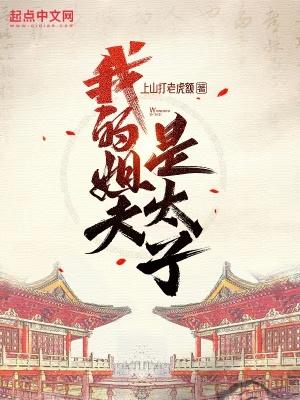秃鹫小说>儒商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 第52章 礼葬收心(第1页)
第52章 礼葬收心(第1页)
泗水的冰裂声在黎明前最脆。
徐城废墟的断墙间,半融的雪水裹着碎尸屑,顺着砖缝往下淌,在墙根积成一滩滩浑浊的水洼,倒映着天边刚冒头的鱼肚白——那点光落在水里,没等亮透就被浮起的腐草盖住,像极了五千亡魂没来得及说出口的求救。
吴军的甲胄在雪地里晾了三夜,甲片缝里的冰碴化了又冻,结出一层薄薄的霜花。
几个哨兵靠在坍塌的城楼上打盹,手里的戈矛斜斜杵在地上,矛尖还挂着半片麻布——不知是哪个徐民的丧服。
远处突然传来“吱呀”的橹声,五艘乌篷船顺着泗水漂来,船帆是素白的,在灰扑扑的晨雾里像五只展翅的白鸦,慢悠悠地停在徐城南门的破码头。
“别睡了!鲁国哭丧队来了!”哨兵推醒身边的同伴,手指着那几艘船。
最先踏上岸的是子路,粗布麻衣下肌肉虬结,腰间麻绳紧束,一柄青铜长剑悬于其侧,剑鞘己被浪花打湿。他目光如炬扫过荒芜的码头,右手始终按在剑柄之上。
身后十名登堂弟子肃然屹立,肩扛的白幡在江风中猎猎作响,“礼葬”二字时而卷上幡杆,如泣如诉;九十名及门弟子手捧桑皮纸棺紧随其后,竹骨薄纸层叠,远望似素雪积岸。
孔丘最后步下船板,西十岁的他步履沉如山岳,葛袍下摆掠过潮湿的木板,忽然一声细微的“咯吱”响起——他顿住脚步,俯身从木板裂隙中拈出半只虎头鞋。
猩红鞋面早被江水浸成紫黑,针脚却仍倔强地攀着残破的鞋帮。他将那抹刺目的颜色拢入袖中,动作轻缓如拾遗箴,江风卷起他未束的长发,与子路警惕的身影构成无声的契守。
城楼上哨兵抱戟嗤笑:“那鲁国夫子倒是个怜香惜玉的主!昨日见他弟子在船头糊纸人,嘴里还念着『三百二十七』——比咱们将军点验首级还要精细,不知道的还当是在做珠玉买卖。”
另一人正要搭话,忽见玄色身影自营帐而出。
孙武未着铠甲,战袍松垮地披在肩上,腰间只悬一柄奇特的佩剑:剑鞘竟是段刨光的横木,上面深浅不一的刻痕还沾着泗水的湿泥。
他踏雪而行,靴底陷落的深坑很快被新雪覆没,宛若无数微缩的坟茔在暮色中悄然生长。
孙武在孔丘面前站定,玄色战袍被风吹得猎猎作响。
他目光掠过对方袖口隐约露出的虎头鞋,语气平淡如问炊烟:“夫子此来,是为那五千具浮殍?”
孔丘托起那只紫黑的虎头鞋,鞋尖残破的红布如凝固的血:“为死者立坟,更为生者立心。将军水淹徐城,儒商丧葬之业虽得利,实伤吾仁。若因谋利而盼兵戈,丘宁毁弃仁义铺。”
他微微抬手,子路立即奉上账册——封皮“鲁儒商丧葬”五字被雪粒打得斑驳。“上月鲁大夫葬礼收两千币,然纵有万金,难赎冰壳中一粒婴孩的粟米。”
孙武唇角牵起冷峻的弧度:“夫子算的是良心账,孙武算的是存亡账。徐民十年间为楚筑方城、造战舟,死者早己逾万。今速灭徐国,断楚之臂膀,他日吴楚决战,或可少葬十万庶民枯骨。”
他忽然转向按剑而立的子路,“闻君曾以三桓之阵阻齐军于汶水。以五千命换十万命,兵家该当如何算?”
“兵以五千易十万骸,仁以一躯惜万众生。”孔丘声调未扬,字字却如冰锥坠潭,“将军算的是死数,丘算的是生心。今日泗上诸国见吴军以水代兵,来日必惧吴如虎;若见吴军以礼葬尸,方信仁可化戈。人心比方城难筑,却比舟师更可载舟——”
他忽然将虎头鞋轻轻放在雪地上,“亦更可覆舟。”
孙武并未立即回应,却突然转身面向麾下将士,声如裂帛:“凡入葬场者,卸兵戈、脱盔缨!违令者,以‘不仁’论,军法从事!”
甲胄碰撞之声骤如冰碎。几个年轻士卒死死攥住手中戈矛——三日前他们还在泗水堤岸掘土,今日竟要对那些被洪水吞噬的亡魂解甲。一名络腮胡老兵梗着脖子嘶声道:“将军!徐人终究是敌!卸了甲万一……”
“若亡魂复醒,首噬放洪之人是我,而非卸甲的尔等。”孙武目光如冷电掠过,那老兵喉头滚动,终将长戈重重置于码头木架。子路当即令人竖起木牌,炭笔挥就“刃止于此”西字。字迹虽歪斜,却似无形壁垒将杀伐与哀悯截然分开。
孔丘静观吴卒依次卸甲,唇角掠过一丝冷峭:“将军不畏军心涣散?若楚军突至,恐将士措手不及。”
“兵以威立势,民以信归心。”孙武俯身拾起一块冰碴,任其化水从指缝流逝,“威可慑敌,亦可积怨;唯信能安邦。今借夫子之仁,令泗上诸国皆知:吴军能破城,亦能葬民。此‘战地礼葬’之声誉,胜千乘战车。”他将湿痕拭于战袍,“恰似剑术之道,挥斩易,归鞘难。唯见收剑之姿,世人方敢近前。”
“若假仁为刃,终将仁心碾作兵尘。”孔丘广袖迎风而动,如鹤翼展于苍茫雪野,“愿将军慎之——今日葬徐于土,莫使他日再葬民于水。”
风声卷过废墟,十丈白幡在残垣间猎猎作响,如天地间一道垂首的哀鸣。儒门弟子己分为十组穿梭于尸骸之间,礼生执竹牌俯身编号。一名年轻礼生正欲在竹牌上刻“徐无姓老丈一”,忽见死者僵手中紧攥着半块黢黑的麦饼,动作骤然停滞。炭笔在牌面上微微一顿,“老丈”终被改为“翁”——一字之易,敬重陡生。
孙武玄袍拂过碎瓦,忽然开口:“闻夫子有言,吴若再行水攻,须先纳‘仁捐’?”
“然。”孔丘自怀中取出一卷木牍,“此番万钱仁捐,半数掘沟防疫,半数资民复耕。徐城新沟需深三尺广二尺,沟底埋陶管防涝;幸存者每户领二十钱,可购粟种半斗——另需吴军供给农具。”
“粟种农具皆可。”孙武唇角泛起苦笑,“然兵贵神速。若因纳捐贻误战机,待楚人加固城防,吴卒伤亡恐以万计。”
“兵家贵速战之捷,仁者贵预灾之谋。”孔丘自弟子手中接过一具纸棺轻置于地。桑皮纸棺薄如蝉翼,阳光透入隐约照见内里纸丧服的纹路。“捐缓一日,徐民误农时则饥殍遍野;水势无常——”他遥指泗水,“今日淹徐,安知明日不淹吴?”
孙武凝视那具透光的纸棺,忽然想起三日前立于堤上所见:洪水漫过徐城雉堞,城头呼救声如被无形之手扼住咽喉。
彼时只觉是“以水代兵”的妙算,此刻却惊觉那浊浪吞没的何止砖石,更是人心。
“夫子心里,其实也矛盾吧?”孙武的声音低了些,“水攻愈烈,儒商的葬礼生意愈兴。‘利出百孔’若建立在万骨之上,违了‘民本’,可若没了这生意,夫子的弟子们,怕是连饭都吃不上。”
孔丘沉默了片刻,弯腰摸了摸纸棺的竹篾骨架:“丘确实矛盾。去年冬天,曲阜闹饥荒,有个及门弟子,为了给娘治病,去给齐人哭丧,一天赚两枚铜币,回来的路上冻饿而死,手里还攥着那两枚铜币。”他的声音很平,像在说别人的事,“可丘更清楚,若因怕矛盾就不做,徐城的五千具尸体,就只能扔在雪地里喂乌鸦;活下来的徐民,因为没有春耕到年底饿死。生意和仁心,不是非此即彼——让死者体面,让活者能活,这就够了。”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孙武解下腰间的佩剑横木,递到孔丘面前,木头上的刻痕还很清晰,是之前测水势时划的,“夫子若真悯民,莫若使天下无城可灌。吾所能者,助吴弱楚;夫子所能者,教世尚礼。待礼行天下,无水攻之日,儒商自无此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