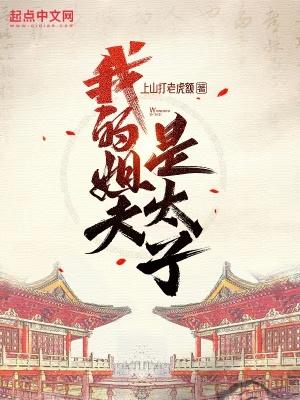秃鹫小说>秦朝大将王翦一生 > 第77章 祁连终章 居延泽谜 这芦苇写天书(第2页)
第77章 祁连终章 居延泽谜 这芦苇写天书(第2页)
“找个会唱楚地歌谣的人来。”王翦当即下令。
李老汉连滚带爬地跑出传舍,一刻钟后领来个年轻女子。她穿着洗得发白的粗布衣裙,梳着楚地特有的双丫髻,发间插着一根骨簪,手里抱着个陶罐,罐口用麻布封着——那是楚地人盛放粮食的习惯。“这是阿楚,上个月从蕲县逃来的,爹娘都死在途中了,平日里常唱楚歌解闷。”李老汉的声音里带着怜悯。
阿楚怯生生地站在案前,目光刚扫过丝帛上的童谣,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往下掉,砸在陶罐上发出轻响:“这是楚地的《怀儿歌》,去年开春就传开了……货郎们走村串户都在唱,还有下阕呢。”她用袖口擦了擦眼泪,清了清嗓子,歌声婉转悲凉,带着浓浓的楚地方言口音,尾音拖得很长,像芦苇荡里的风:
“星垂野,露沾裳,
龙旗卷过汨罗江。
风瑟瑟,水汤汤,
汉家天下万年长。”
歌声落下时,蒙武突然脸色一变,猛地按住桌案:“这曲调……”他用手指在案上轻轻敲击,跟着哼唱起来,“不对,这起调的‘黄钟宫’,转折的‘太簇角’,还有收尾的‘仲吕羽’,和我去年在沛地听过的一首民歌很像,只是节奏慢了一半!”
王翦的目光落在那些律吕符号上,忽然想起疏勒河发现的青铜铸模上刻着的“汉祚绵长”,想起黑水河碑上的“赤帝子斩白蛇”——所有线索都像百川归海,指向一个可怕的事实:有人在楚地散布童谣,用谶言制造“天命归汉”的舆论,用音乐传递秘密信息,而这一切的目标,都是推翻大秦,建立所谓的“汉家天下”。他看向窗外,居延泽的芦苇在正午阳光下泛着金色,却像无数把暗藏的利刃,透着刺骨的寒意。
【三:曲谱溯源,风歌先兆音】
暮色渐浓,传舍内点起了三盏油灯,昏黄的灯光将丝帛上的符号照得愈发清晰,投在墙上的影子忽明忽暗,像跳动的音符。蒙武找来新的竹简,用狼毫笔蘸着朱砂,按照律吕记谱法的规则,将那些针尖刻出的符号逐一转化:“黄钟宫、大吕商、太簇角、姑洗徵、仲吕羽……”每写一个,就用指尖轻轻敲击桌面,模拟出音调的高低起伏,油灯的火苗也跟着微微晃动。
阿楚坐在角落的草席上,双手紧紧绞着衣角,陶罐放在腿边。当蒙武敲到“太簇角”时,她突然抬起头,眼里还带着未干的泪痕:“这个调子……我在沛地听过!去年跟着爹娘逃荒路过丰邑时,见过一个穿亭长服饰的人,在田埂上唱过类似的歌,只是词不一样,节奏也更有力些。”
“亭长?”蒙恬猛地从草席上起身,快步走到阿楚面前,双手抓住她的胳膊,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是不是姓刘?高鼻梁,下巴上有颗黑痣,说话带着痞气,还总说自己是‘赤帝之子’?”
阿楚被吓得一哆嗦,连连点头,眼泪又掉了下来:“是、是姓刘!他身边跟着个红脸大汉,还有个卖狗肉的,那天他们在田埂上喝酒,刘亭长就站着唱,说‘总有一天要让天下人都听他唱歌’……”
王翦的呼吸猛地一滞,端着陶杯的手微微颤抖,杯中的粟米酒晃出了几滴。刘邦!又是这个名字!从嘉峪关的“泗水亭”刻石,到黑水河底的“汉高祖”残碑,再到阿楚口中自称“赤帝子”的亭长,这个沛县小吏的影子,竟像鬼魅般缠绕在所有线索里。他接过蒙武手中的竹简,指尖划过那些朱砂写就的律吕名称,忽然想起二十年前随军征战楚地时,在蕲县听过的一首民谣,曲调与这些音符组合出的旋律隐隐相合,只是那首民谣更为粗犷豪放,带着破釜沉舟的决绝。
“你再唱一遍,把调子唱准些,节奏放慢。”王翦对阿楚说,声音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阿楚定了定神,深吸一口气,再次唱起《怀儿歌》。这次蒙武跟着一起哼唱,手指在竹简上打着拍子,渐渐加快了节奏,调整着音调的高低。当唱到“汉家天下万年长”的收尾音时,蒙武突然停住了,眼睛瞪得大大的,手里的狼毫笔“啪嗒”掉在竹简上,朱砂晕开一片:“将军!这、这曲调跟……跟将来若刘邦称帝,可能创作的《大风歌》简首一模一样!”
“胡说!”蒙恬厉声呵斥,一把揪住蒙武的衣领,“当今陛下龙体康健,大秦基业稳固,何来‘刘邦称帝’之说?你这是惑乱军心!”
蒙武却用力推开蒙恬的手,捡起竹简在案上敲击出急促的节奏:“你听!这起调的‘黄钟宫’厚重沉雄,正是帝王之歌的规制;转折处‘太簇角’陡然拔高,带着睥睨天下的气势;收尾‘仲吕羽’余音绕梁,暗藏长治久安的祈愿!《乐记》有云‘乐与政通’,这曲调绝非民间随意谱写,分明是按照最高规格的宫廷乐律创作的!”他曾在乐府研读三年,对音律的敏感远超常人,“而且这旋律的骨架,与楚地《九歌》中的《东皇太一》同源,却又融入了沛地民歌的质朴,分明是为刘邦量身定做的天命之乐!”
王翦沉默着走到窗边,推开木窗。居延泽的夜色己浓,漆黑的芦苇荡像无边的墨汁,风穿过苇叶,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无数人在低声吟唱。他想起黑水河碑上“赤帝子斩白蛇”的刻字,想起丝帛上“项家枪,刘家剑”的字句,想起阿楚口中刘邦那志得意满的神态——所有的细节都在编织一张巨大的网,一张针对大秦、针对始皇帝的阴谋之网。
“李老汉,”王翦转身看向缩在角落的啬夫,“那货郎除了留下芦苇,还有没有别的痕迹?比如特殊的气味、掉落的物件?”
李老汉连忙爬起来,努力回忆着:“有!他的布包角沾着些黄色粉末,像是硫磺,还有点铁锈味!小人打扫时还发现了半截马掌,上面刻着个‘项’字,和将军您桌上的令牌字迹一样!”他顿了顿,又补充道,“还有他的马蹄印,朝着居延泽西岸去了,那边有个废弃的烽火台,是十年前蒙恬将军北击匈奴时留下的,后来被浑邪部抢去过,听说他们用狼烟传递消息!”
蒙恬立刻抄起案上的青铜剑,剑鞘撞击在陶杯上发出脆响:“末将去烽火台看看!若能抓到活口,定能问出阴谋!”
“带上十名亲卫,多备弓箭,小心行事。”王翦叮嘱道,目光落在那枚“项”字令牌上,指腹着冰冷的青铜表面,“项氏在楚地经营多年,此次竟敢勾结匈奴,恐怕烽火台里不止是信使那么简单。记住,先探虚实,切勿轻举妄动。”
蒙恬领命离去后,传舍内只剩下王翦和蒙武。蒙武继续研究曲谱,忽然“咦”了一声,拿起最底下那片竹简——背面竟用秦篆刻着几行极小的字,像是用针尖刺上去的,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曲谱传沛,三户响应,沙丘待变,共举大事。”
“沙丘!”王翦猛地攥紧了拳头,指节发白。沙丘平台是始皇帝东巡的必经之地,那里地势低洼,多有沼泽,正是设伏的绝佳地点。结合黑水河碑上“沙丘有变”的刻字,一场针对始皇帝的刺杀阴谋,己经在暗中酝酿成熟。他看向蒙武,眼中闪过一丝厉色:“看来我们必须立刻启程,赶在陛下东巡抵达沙丘前,揭穿这场阴谋!”
【西:泽底烽火,楚秦暗交锋】
三更时分,传舍外突然传来急促的马蹄声,伴随着亲卫的低喝。王翦立刻拔出腰间的陨铁剑,剑身在油灯下泛着冷冽的寒光——这是当年始皇帝赏赐的宝剑,曾随他征战无数,剑刃上还留着楚兵甲胄的划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