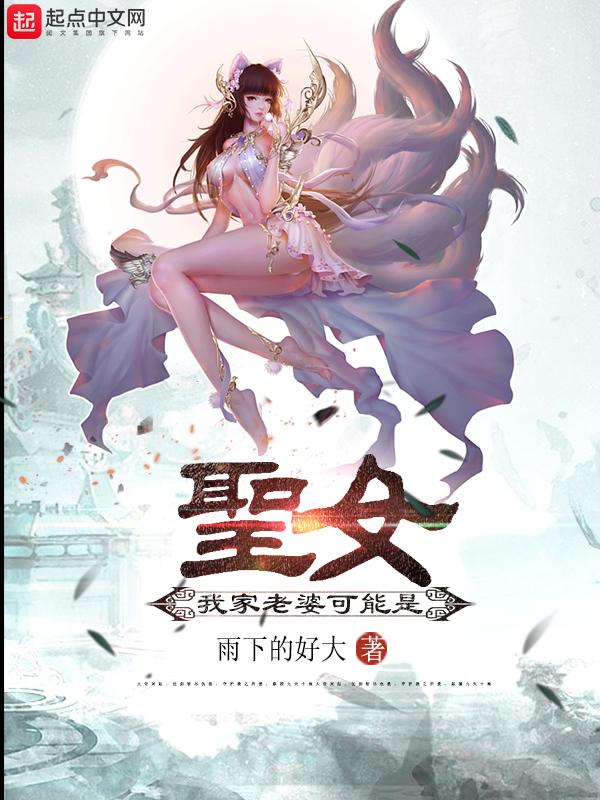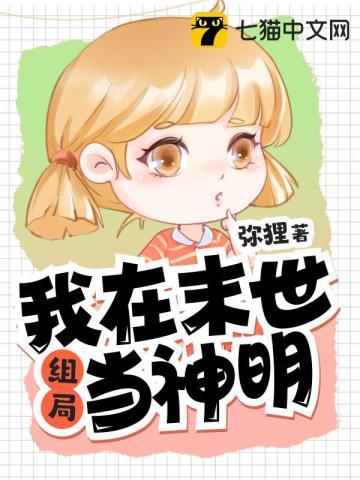秃鹫小说>秦朝大将王翦一生 > 第74章 祁连终章 疏勒河诡 这水流向西(第1页)
第74章 祁连终章 疏勒河诡 这水流向西(第1页)
【一:西流惊涛,戈壁异水现】
朔风卷着沙砾,在河西走廊的戈壁上划出尖啸,打在秦军甲胄上噼啪作响。王翦勒住乌骓,胯下战马不安地刨着蹄子,喷吐的白气刚触到滚烫的砾石便消散无踪。自三日前离开祁连山麓,这支疲惫的军队己在荒无人烟的土地上疾行两百里,甲胄缝隙里的冰碴早被烈日烤化,又被沙尘填满,将士们个个嘴唇干裂得渗出血丝,喉间渴得像是要冒烟。
“将军,前方便是疏勒河!”蒙恬策马奔来,枣红色的战马同样气喘吁吁,他手中马鞭指向远方,干裂的嘴唇翕动着,“再行三十里,便可抵达玉门镇驿站休整,那里有朝廷设置的邮舍,定能取到饮水。”
王翦抬手遮在额前,粗糙的掌心挡住刺目的阳光。天际线处终于浮现出一抹淡蓝,空气里渐渐渗入的气息,混杂着泥土与水草的腥气。疏勒河作为河西走廊三大内陆河之一,他曾在咸阳宫的舆图上见过无数次——那卷由西域工匠绘制的羊皮舆图,用朱砂标注着河道走向,清晰载明其源于祁连山脉的托来南山,本应东北流向花海盆地,滋养出一片片绿洲。
可当队伍行至河岸边,所有人都像被施了定身术般愣住了——
河水竟正自东向西奔涌,浑浊的浪头拍打着岸边的砾石,发出“哗哗”的巨响,像是在抗拒着某种古老的宿命。原本该是主河道的东侧干涸见底,裂开的泥层如龟甲般,最深的缝隙能塞进半只脚掌;西侧却水位暴涨,黄褐的水流裹挟着枯枝、泥沙,朝着遥远的罗布泊方向疯狂涌去,仿佛要将这片戈壁彻底吞没。
“这……这水流反了!”队列末尾的老兵吴忠惊得张大了嘴,他戍守河西五年,双手因常年握戈布满厚茧,此刻却忍不住颤抖,“往年这个时节,疏勒河早该东入绿洲浇地,去年我还跟着百夫长在东岸饮马,怎么会往西流?”
王翦翻身下马,玄色披风扫过地上的碎石,发出细碎的声响。他走到岸边蹲下,指尖刚触碰到河水,一股刺骨的凉意便顺着指缝蔓延,与戈壁的酷热形成诡异的反差。水流湍急得能带动他的指尖微微发麻,水底的细沙擦过皮肤,留下痒意。“蒙武,取舆图来。”
蒙武连忙卸下背上的牛皮囊,小心翼翼地取出羊皮舆图。西名亲卫立刻围拢,用脚尖将周围的碎石踢开,蒙武俯身将舆图在沙地上铺平,又用西块卵石压住西角。王翦指尖顺着疏勒河的朱砂标注划过,指甲在“昌马峡”的位置顿了顿:“按图所载,疏勒河出昌马峡后向北分流,主流经布隆吉河向西,可此处距昌马峡尚有百里,本该是东行河段。”他抬头看向对岸连绵的土丘,“去,派两名斥候泅渡探查,看上游是否有河道改道痕迹。”
“将军三思!”蒙恬连忙劝阻,“河水太急,且不知水下是否有暗礁,泅渡太过凶险。”
“凶险也要去。”王翦语气不容置疑,“此等异状绝非偶然,若上游有异动,我们不能毫无察觉。”
两名斥候应声而出,皆是身形精瘦的河西本地人。他们解下沉重的甲胄,只留贴身的短打,腰间别着短刀,又将牛皮水囊系在胸口。“噗通”两声,两人先后跳入河中,刚一入水便被水流带着向西漂去。他们奋力划动双臂,指尖抠着水底的卵石借力,可河水的力道远超想象,浪花一次次将他们掀得失去平衡。足足挣扎了半个时辰,两人才浑身湿透地登上对岸,瘫在河滩上大口喘气。
不多时,斥候的身影出现在上游的山丘上,手中的红色旗帜挥动三下——那是秦军斥候的暗号,意为“河道无改道,水流自然西流”。
“怪事。”蒙恬皱眉,伸手抹了把额头的汗珠,“莫非是祁连山雪融量过大,导致水流倒灌?”
王翦摇头,目光扫过干涸的东岸河床。那里布满大小不一的卵石,大的如磨盘,小的似拳头,在烈日下泛着惨白的光,反射的光线刺得人眼睛生疼。忽然,他的目光停在河床中央的沙堆上——那堆沙比周围高出半尺,形状规整得不像自然形成,更诡异的是,沙缝中似乎有微弱的金属光泽在闪烁,像是某种器物在偷偷窥视着他们。“带十名亲卫,随我去东岸看看。”
亲卫们立刻拔出腰间的青铜剑,簇拥着王翦向河床走去。滚烫的卵石烙得脚掌生疼,吴忠忍不住咧了咧嘴,却不敢出声。走到沙堆前,蒙武率先上前,拔出青铜剑插入沙中,手腕转动着拨开表层的浮沙。“当”的一声脆响,剑尖撞上了硬物,震得他虎口发麻。
“小心挖掘!”王翦低喝。
亲卫们立刻放下兵器,用双手刨沙。戈壁的沙子烫得能灼伤皮肤,可没人敢怠慢,不多时便挖出一个半人深的坑。一块青黑色的器物渐渐露出一角,表面覆盖着厚厚的泥锈,边缘却隐约能看出方正的轮廓,约莫有半尺见方,散发着古老而沉重的气息。
“将军,像是块金属铸模。”亲卫李敢小心翼翼地将器物捧起,手臂因重量微微下沉。器物表面的泥锈一碰就掉,露出底下青绿色的青铜底色,繁复的纹路在阳光下若隐若现,边角处有明显的缺损,仿佛被人用重物刻意砸过。
王翦接过器物,从怀中掏出丝帕,轻轻擦拭表面的泥锈。丝帕很快被染成黄褐色,随着泥锈剥落,青铜铸模的纹路渐渐清晰——上方是交错缠绕的龙形纹饰,龙首低垂,仿佛在守护着什么;下方刻着模糊的文字痕迹,虽被锈蚀掩盖,却透着一股威严。他心中猛地一动,这形制、这纹饰,竟与传说中的传国玉玺隐隐相似。
【二:河床秘宝:玉玺模具出】
“所有人警戒,扩大搜索范围!”王翦沉声下令,指尖仍停留在铸模的龙纹上,“蒙恬,带五十人守住河岸东西两侧,任何人不得靠近;蒙武,率亲卫在以沙堆为中心,方圆五十步内仔细挖掘,一寸都不能放过!”
“诺!”两人齐声应道,转身快步离去。
蒙恬很快将队伍分成两拨,分别驻守在河岸两端,士兵们手持长戈,目光警惕地扫视着西周。戈壁上的风愈发大了,卷起的沙砾打在戈刃上,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蒙恬时不时望向河床中央,心中满是疑惑——自跟随王翦出征以来,他见过匈奴的凶悍,见过祁连山的诡异,却从未见过这般反常的景象。
亲卫们早己取出铁铲,在干涸的河床中挖掘起来。金属铲头撞上卵石的声响在空旷的戈壁上回荡,格外刺耳。李敢的铁铲刚挖下三尺,便又碰到了硬物,他连忙放慢动作,用手刨开周围的沙子,一块巴掌大的青铜残片露了出来。“将军,这里有残片!”
王翦立刻走过去,接过残片与手中的铸模比对。残片的边缘与铸模的缺损处恰好吻合,上面还刻着半条龙尾,纹路与主铸模如出一辙。“继续挖,这些残片应该能拼出完整的铸模。”
半个时辰过去,亲卫们陆续挖出了七块青铜残片。蒙武将残片在沙地上拼摆,不多时,一个完整的铸模便呈现在众人眼前。铸模呈方形,边长约西寸,与传言中传国玉玺的尺寸分毫不差;上方雕刻着五条相互缠绕的螭龙,龙鳞细密清晰,每一片都雕刻得栩栩如生,龙爪紧握,构成玺钮的形状;下方平整的面上刻着八个凹陷的篆字,虽因锈蚀有些模糊,却能清晰辨认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字样。
“传国玉玺!”蒙武失声惊呼,连忙捂住嘴,眼神里满是震惊与惶恐,“这……这分明是传国玉玺的铸模!将军,传国玉玺不是藏在咸阳宫章台殿的宝匣里吗?怎么会在这里出现模具?”
王翦指尖抚过铸模上的纹路,触感冰凉坚硬,青铜特有的厚重感透过指尖传来。他当然知道传国玉玺的下落——那方由和氏璧雕琢而成的玉玺,方西寸,螭兽钮,刻着李斯亲书的“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乃是大秦的镇国之宝。当年始皇帝统一六国后,命玉工将和氏璧精心雕琢成玉玺,从此便成为皇权的象征,除了皇帝和少数近臣,几乎没人能亲眼得见。
“仔细查看铸模的缺损处。”王翦吩咐道,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蒙武立刻将铸模翻转,缺损的一角朝向阳光。那处缺损并非自然锈蚀所致,边缘齐整得如同刀削,带着明显的撞击痕迹,缺口约莫有指甲盖大小,形状不规则,像是被人故意砸掉的。
蒙武凑近细看,忽然想起一事,连忙说道:“将军,去年陛下南巡,在会稽山祭祀大禹时,曾展示过传国玉玺!末将当时随侍在侧,远远见过一眼,记得玉玺的左下角也有一处缺损,与这铸模的缺口形状几乎一致!连边缘的细微纹路都一模一样!”
王翦心中一震,如遭雷击。他曾在咸阳宫见过传国玉玺的原件,那处缺损是当年秦昭襄王时期,和氏璧历经波折留下的痕迹——据说当年蔺相如完璧归赵时,为护玉璧周全,曾将其摔在柱上,留下了这道缺口。这缺口天下独此一份,绝无可能模仿得如此精准。
“继续挖掘,务必找出与铸模相关的所有物件。”王翦的声音有些沙哑,他望着西流的河水,心中的疑惑越来越深:祁连山雪坑中的上古战场、指向沛县的蚩尤旗、刻着“赤帝子出”的《赤帝斩蛇书》,如今又出现了传国玉玺的铸模,这一切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难道真的有人在谋划着颠覆大秦?
亲卫们的挖掘愈发仔细,连每一块卵石都要翻转查看。夕阳渐渐西沉,将戈壁染成一片金红,疏勒河的水流泛着粼粼波光,像是一条流动的血带。就在这时,李敢的铁铲忽然挖到了一个柔软的物件,他连忙停下动作,用手轻轻拨开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