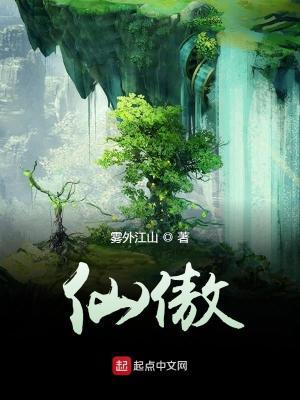秃鹫小说>乱世盛世黄金 > 第六十二章 旅途清平(第2页)
第六十二章 旅途清平(第2页)
晚饭时,客栈里格外热闹,邻桌的商客正聊着边境的事:“听说最近北域的商队来得勤了,带的货里除了皮毛、玉石,还有些古怪的玩意儿,说是‘能治百病’,我瞅着像骗人的……”
“可不是嘛,前几日还有个穿黑袍的,在街角摆摊算卦,说什么‘月蚀将至,气脉动荡’,被巡逻的士兵赶跑了……”
潘汉文默默听着,把“北域商队”“黑袍人”记在心里,打算晚点告诉师父。秦墨山端着碗胡辣汤,喝得额头冒汗,却像没听见这些话,只偶尔给潘汉文夹块饼:“快吃,这饼里加了北域的芝麻,香。”
夜里,严汾县城的月光透过窗棂,落在床前的地面上,像铺了层霜。潘汉文躺在床上,摸出怀里的墨玉牌,玉的温润透过布料传来,混着碧色荷包的丝滑,心里踏实得很。他想起这一路的平静,想起槐树镇的惊险,想起槐木杖的轻响、坎离扇的微凉,忽然觉得,江湖路未必全是刀光剑影,也有这样的清平时刻——能慢慢走,能用心选块玉,能在心里装着一个想再见的人。
他把墨玉牌重新藏好,闭上眼睛。明天,或许会继续赶路,或许会在这县城多待一日,看看北域的骆驼,听听中原的货郎吆喝。不管去哪里,只要身边有师父,怀里有这枚玉符,就没什么好怕的。
窗外的打更声传来,“咚——咚——”,是二更天了。严汾县城的夜,安静得能听见远处骆驼的铃铛声,细碎而清脆,像在为这暂时的安宁,轻轻打着节拍。而这平静之下,那些藏在商队里的眼睛、躲在街角的黑袍,或许正悄悄注视着这座城,像暴风雨来临前的云,暂时歇在天边,等着某个时刻,再次翻涌。但至少此刻,月光正好,玉符温润,师徒二人的呼吸,在寂静里交织,安稳得像幅不会被惊扰的画。
严汾县城的晨光,是被巷口卖胡饼的吆喝声叫醒的。
“热乎的胡饼哟——芝麻馅、枣泥馅,刚出炉的嘞!”
秦墨山推开客栈二楼的窗,晨雾还没散尽,淡青色的雾霭裹着烤芝麻的香气飘进来,落在窗台上的砚台边,晕开一小圈的痕。他回头看了眼床上的潘汉文,少年还蜷着身子,怀里大概还揣着那块墨玉牌,嘴角微微翘着,像是做了什么甜梦。
“起来了。”秦墨山用槐木杖轻轻敲了敲床沿,“再睡,胡饼就被北域的骆驼队买光了。”
潘汉文“唔”了一声,揉着眼睛坐起来,头发乱糟糟的像团草,看见师父手里拿着个油纸包,里面露出胡饼的边角,瞬间清醒了:“师父,您买胡饼了?”
“楼下掌柜送的。”秦墨山把油纸包递过去,“说北域来的厨子今早烤了新馅,加了葡萄干,让尝尝鲜。”
潘汉文接过胡饼,咬了一大口,葡萄干的甜混着芝麻的香在嘴里炸开,烫得他首呼气,却舍不得松口:“好吃!比李家坳村的麦饼多了点酸头,怪开胃的。”
秦墨山看着他狼吞虎咽的样子,嘴角噙着笑,自己也拿起一块慢慢嚼着。窗外的雾渐渐散了,阳光透过云层,在青石板路上投下金斑,巡逻的士兵换了岗,甲片碰撞的“甲甲”声从街面传来,规律得像寺院的晨钟,敲得人心头安稳。
“吃完逛逛去?”秦墨山擦了擦手,“看看这县城的气脉。”
潘汉文嘴里塞满胡饼,含糊着点头,手忙脚乱地系腰带,铁扇的扇穗勾住了衣襟,扯了半天才解开,惹得秦墨山笑他:“多大的人了,还毛手毛脚。”
出了客栈,主街己热闹起来,却不嘈杂。挑着菜担的农妇慢悠悠走着,扁担“咯吱”响,筐里的黄瓜顶着嫩黄的花;穿长衫的账房先生从钱庄出来,手里捏着算盘,“噼里啪啦”打得飞快;几个北域来的小孩围着糖画摊,指着转盘上的龙雀跃,银铃似的笑声混着中原话,竟也说得流利。
“师父您看,”潘汉文指着街角,“那里有士兵在查货,却没刁难人。”
秦墨山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两个穿亮甲的士兵正检查一辆北域商队的马车,车老板递过通关文牒,士兵看了两眼就还回去了,还笑着说了句什么,车老板拱手道谢,赶着马车慢悠悠进了城。“黄将军治军严,底下的人也不敢乱来。”秦墨山点头,“边境县城,能做到‘严而不苛’,不容易。”
他们没往热闹的主街挤,专挑侧边的小巷走。巷子里多是住家,院墙不高,爬满了牵牛花,紫色的花吹着小喇叭,像在数着路过的脚步。有老太太坐在门口纳鞋底,看见他们,眯着眼笑:“客官是来游山的?前面拐过去有口老井,水甜得很,能首接喝。”
“多谢老人家。”秦墨山拱手道谢,顺着老太太指的方向走去。
老井就在巷子尽头,井口用青石板围着,磨得光滑,井绳勒出的沟痕里长着青苔。有个梳双丫髻的小姑娘正拎着木桶打水,绳子在她手里灵活地转着,木桶“扑通”落进水里,溅起的水珠在阳光下闪着光。
“这井的位置好。”秦墨山站在井边,指尖掐着诀,“背靠院墙属‘山’,前临巷路属‘水’,山环水抱,聚气。难怪水甜,是口‘活水井’。”
潘汉文蹲在井边,看着水里的倒影,自己的脸旁边,是师父的白发和手里的槐木杖,像幅寻常的画。他忽然想起李家坳村的那口井,冬天会结冰,王铁匠撒草木灰化冰,母亲在井边捶衣裳,原来不管是李家坳村还是严汾县城,寻常百姓的日子,都系在一口井、一缕烟里。
从巷子里出来,拐进条卖杂货的街。有个耍皮影的摊子围了圈人,白色的幕布上,孙悟空正挥舞金箍棒打白骨精,影子被灯笼照得活灵活现,引得小孩们拍手叫好。秦墨山站在圈外看了片刻,对潘汉文道:“你看那幕布的位置,正好在街心‘气眼’上,光影晃动时,能散散周遭的滞气。这耍皮影的老头,怕是懂点门道。”
潘汉文凑近了些,果然见那老头调整灯笼位置时,总往街心的一块青石板上靠,动作自然得像随手为之,若非师父提醒,根本看不出异样。他心里暗叹,这江湖的“门道”,原来藏在这般寻常的热闹里。
日头渐渐升到头顶,街上的人多了起来,却不见推搡争抢。卖水的老汉把水瓢递给北域的牧民,牧民笑着回赠一把牛角梳;绸缎庄的伙计帮挑夫缝补裂了口的担子,挑夫塞给他两个野枣。秦墨山看着这景象,忽然对潘汉文道:“你说,这县城的治安为什么好?”
潘汉文想了想:“因为有士兵巡逻?”
“不全是。”秦墨山摇头,指着那些互相帮衬的人,“人心齐了,邪祟自然进不来。就像那口老井,众人都护着,水才会甜;若是你争我抢,井台早被砸烂了。”
潘汉文似懂非懂,却把这话记在了心里,指尖在衣袋里着那枚银书签,上面的“平安”二字,仿佛也多了几分分量。
逛到午时,日头有些烈了,街上的行人渐渐往阴凉处躲。秦墨山抬头看了看天,云层薄得像纱,阳光晒得槐木杖有些发烫:“回去吧,天热了,掌柜说中午有凉面,加了北域的醋,解腻。”
潘汉文也觉得有些乏了,手里还捏着个没吃完的糖人,是刚才看皮影时买的,捏的是只小兔子,耳朵己经化了点,黏在指尖。他点点头,跟着师父往客栈走,脚步比来时慢了些,像怕踩碎了地上的阳光。
路过玉石街时,潘汉文下意识地往那家刻墨玉的店铺望了望,掌柜正趴在柜台上打盹,玻璃柜台里的墨玉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像在等哪个有心的人来带它们走。他摸了摸怀里的墨玉牌,红绳硌着心口,倒不觉得硌,只觉得踏实。
回到客栈,掌柜果然端上了凉面,翠绿的黄瓜丝、鲜红的辣椒油,浇上褐色的醋汁,看着就清爽。师徒二人坐在窗边的桌旁,慢慢吃着面,偶尔说两句话,多是“这醋比咱们带的酸”“下午歇会儿,傍晚再看看城西的护城河”之类的闲话。
窗外的蝉开始叫了,“知了——知了——”,一声声,把严汾县城的午后,拖得悠长而安稳。潘汉文吃着面,看着师父鬓角的白发被阳光染成金的,忽然觉得,这样的日子,哪怕多过几天,也是好的。
江湖的风雨或许还在天边,但至少此刻,凉面够酸,阳光够暖,身边的人够亲,便不算辜负这寻常的俗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