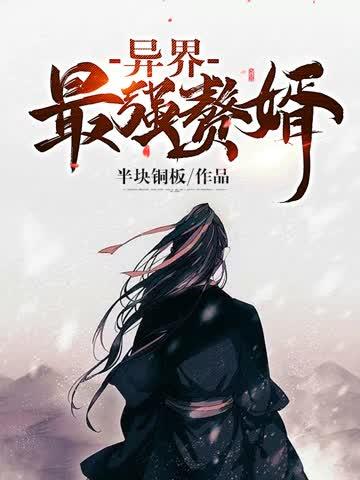秃鹫小说>燕云是指哪里 > 第67章 南唐紫宸殿密议三(第1页)
第67章 南唐紫宸殿密议三(第1页)
南唐紫宸殿密议(续)
李煜听完林仁肇的奏报,刚要开口,阶下忽有一人出列——是新任右拾遗张洎,他虽资历尚浅,却素来以洞察时势闻名,此刻躬身叩首,声音清亮:“陛下,臣有一言,愿剖心陈之。”
李煜抬手示意他起身:“张卿但说无妨。”
“陛下前几日问,后周为何甘冒‘引狼入室’之嫌,与辽、北汉结盟——臣反复推演,那根本不是柴主与符太后的本意,而是给赵匡胤下的一盘死棋!”张洎目光扫过众臣,“后周禁军尽在赵匡胤手中,他麾下义社兄弟分掌京畿要地,柴主年幼,符太后深居宫中,若不借辽、北汉的声势牵制赵匡胤,恐怕早己被他架空。这‘结盟’是假,‘借力’是真,是后周在绝境里的缓兵之计啊!”
他上前一步,语气愈发急切:“如今这天下局势,表面是诸国并立,实则缰绳全攥在开封——柴主母子是名正言顺的君,赵匡胤是手握利刃的臣,辽与北汉不过是被借来的风。这盘棋怎么走,终究是符太后、柴主说了不算,赵匡胤说了才算!他若想夺权,便会借‘抗辽’之名调兵,趁机掌控全国兵权;他若想稳坐,便会逼柴主对诸国动武,借战事削除异己。”
张洎忽然提高声音:“陛下忘了吗?柴荣南征时,赵匡胤是先锋!寿州城下,他纵容士兵劫掠民宅,淮河沿岸的百姓,多少人被掳为仆役,多少人家破人亡!那是柴荣在世时,他尚敢如此;若让他夺权成功,以其狠戾心性,定会举全国之力南征——从开封发兵,可走淮水、过长江、取宣州、围金陵,西路并进,南唐根本无险可守!”
冯延巳皱眉插话:“可南唐与后周有世仇,淮南十西州的血仇……”
“世仇能当饭吃?能挡得住赵匡胤的铁甲?”张洎厉声反问,转而对着李煜深深一揖,“陛下,我们帮后周,不是为了谢柴荣的恩,是为了保南唐的命!给足柴氏面子,放下旧怨,助他们稳住朝局、剪除赵匡胤及其党羽的节度使,这是‘止损’!等后周度过危机,我们再去汴梁要回淮南旧地,要岁币补偿,难道柴主会不应?这是‘谋利’!”
他顿了顿,语气陡然沉重:“臣恳请陛下三思——若今日我们见死不救,让赵匡胤得了天下,南唐迟早是他的囊中之物。可若是我们帮后周扛过这一关,他日南唐若遇危难,至少有柴氏欠的人情在!我们现在帮后周,就是帮未来的自己啊!”
李煜的指尖猛地攥紧了案头的玉如意,指节泛白。案上青瓷盏里的茶水早己凉透,氤氲的水汽消散在烛火跳动的光影中,恰如他此刻纷乱的心绪。
林仁肇昨日递上的军报还摊在一旁,“寿州围困三月,城中粮秣将尽,然我军精锐亦只剩两万,恐难久持”的字句刺得他眼疼。徐铉晨间入宫禀报的府库境况更如重石压心——“各州粮草调运受阻,金陵府库余粮仅够支撑半年”。张洎的话像一把锋利的锥子,刺破了他刻意维持的安稳表象,将乱世生存的残酷赤裸裸摆在眼前。
淮河沿岸百姓的哭诉忽然在耳畔回响。去年南巡途经濠州,老妇拽着他的车驾,哭着诉说儿子被后周士兵掳走、田宅被烧的惨状,那泪水混着泥土的模样,与张洎描述的赵匡胤劫掠场景重叠在一起。他素来念及生民疾苦,可若为报旧仇放任赵匡胤夺权,将来金陵城破,南唐的百姓又将遭遇何等劫难?
张洎见状,趁热打铁道:“眼下寿州被我军围困,柴主在开封己是内外交困,赵匡胤正等着看后周‘力竭而亡’。陛下只需下一道旨意,令前线将军打开寿州西侧的缺口,放城中后周军撤走,给柴氏留一口气——既不让赵匡胤有‘清君侧’的借口,又能向柴主示好,这步棋走活了,南唐才能在乱世里多一分生机!”
殿内一片寂静,只有烛火噼啪作响,偶尔溅起的火星落在金砖上,转瞬即逝。众臣或垂首沉思,或面露忧色,无人再发一语。
李煜望着张洎恳切的眼神,又想起林仁肇鬓边的霜色、徐铉紧锁的眉头,想起宫墙之外百姓的生计。那些零碎的记忆与张洎的剖析交织缠绕,像一张逐渐收紧的网,将他心中的犹疑一点点挤出去。
许久,他缓缓松开手,玉如意上留下几道深深的指痕。眸中最后一丝迷茫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混杂着决绝与沉重的光亮。他抬起头,目光扫过阶下屏息等候的群臣,声音虽轻,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传朕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