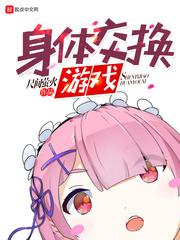秃鹫小说>王妃请自重皇后 > 第212章日上三竿(第2页)
第212章日上三竿(第2页)
这是当年“暗火计划”救援队的旗号。
消息传回内陆时,已是三天后。全国邮筒收到大量匿名来信,内容各异,却都提到了同一个现象:每当有人对着邮筒说出真心话,附近的见心莲便会无风自动,花瓣散发出淡淡蓝光,持续数息方散。
科学家组建专项小组研究,最终得出结论:这种植物的细胞结构中含有微量共振晶体,能对特定频率的人声产生反应。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些晶体的成分与百年前沈清璃遗骸中的骨粉高度吻合。
“她把自己的生命融进了土壤。”生态学家在报告中写道,“这不是生物学奇迹,而是一场跨越时间的倾听。”
与此同时,心灯社总部陷入前所未有的动荡。曾经靠编造苦难博取流量的主播们集体辞职,其中三人联名发表公开信:
>“我们曾以为眼泪是用来卖钱的。直到看见一个真实饿晕的女孩躺在医院走廊,而全网热搜却是‘某明星离婚细节曝光’。那一刻我们才明白,不是观众冷漠,是我们切断了真实的通道。”
信中提议解散现有运营体系,转型为公益信息平台,专门收集并核实民间求助信息,免费对接资源。此议一经发布,竟获得超过八十万普通网民联署支持。
守烛文书局为此召开特别会议。老学究翻阅着各地送来的记录,手指颤抖地指着地图上新增的邮筒数量??已有六百四十二座,覆盖一百七十三个市县,且每日以平均五座的速度增长。
“这不是运动,”他喃喃道,“这是觉醒。”
他下令启动“薪传仪式”的第二阶段:允许民间自发申请成为“承声点”,即设立邮筒并定期整理信件的志愿者站点。条件只有一个:必须亲自阅读每一封来信,并在七日内给予回应??哪怕只是写一句“我收到了”。
第一批获批的站点中,有一处格外引人注目:西北戈壁滩上的废弃哨所。那里常年风沙肆虐,最近的城镇也在两百里外。申请者是一位退伍老兵,他在表格备注栏写道:
>“我在这里守了三十年边防,听过无数战友的遗言。可从来没人问我,我有没有想说的话。现在我想试试,能不能做个听话的人。”
与此同时,陈砚已踏入西域荒原。
他一路西行,穿越沙漠与雪山,只为寻找传说中的“静语窟”??据《万灯志》记载,那是沈清璃晚年闭关之地,洞壁刻满了未能寄出的信。每一笔都是以指尖蘸血写成,历经百年仍未褪色。
抵达那日,正值沙暴歇息。夕阳将整片戈壁染成金红,仿佛大地在燃烧。陈砚推开石门,尘埃簌簌落下。洞内昏暗,唯有几缕光线透过裂缝洒下,照亮了密密麻麻的文字。
他一步步走过,目光扫过那些熟悉的字迹:
>“若世人皆沉默,我愿做第一声呐喊。”
>
>“善不是强者施舍,而是弱者彼此搀扶。”
>
>“不要崇拜光,去做那个点灯的人。”
他的呼吸渐渐沉重。走到最深处,他看见一面完整的石墙,中央刻着一行最大最深的字:
>“陈砚,你终于来了。”
他猛地跪下。
这不是预言,而是等待。她早就知道他会来,就像知道他会归来长安、重建守烛脉络、亲手埋葬引心笛一样。
他颤抖着手掏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翻开一页页写满却从未寄出的信。有道歉,有忏悔,有思念,也有疑问。他一字一句读出来,声音低哑却清晰,在空旷山洞中回荡。
读完最后一封,他忽然听见身后有动静。
转身望去,洞口站着一个小男孩,约莫十岁,穿着破旧棉袄,手里拎着一只迷你版的黑邮筒,是用铁皮罐改装的。
“叔叔,”孩子怯生生地说,“我可以把信放这儿吗?”
陈砚点头,挪开身子。
孩子走上前,小心翼翼地将一封信塞进石缝,然后双手合十,闭眼默念了几句。做完这一切,他抬头问:“你会帮我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