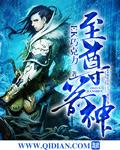秃鹫小说>边关兵王从领娶罪女开始崛起陵川 > 第468章 奉旨入宫(第1页)
第468章 奉旨入宫(第1页)
“将军快走,这里交给咱家!”刘恩赐脚步迅疾地赶来,手中长鞭再次挥出,如灵蛇般缠向黑衣人。
凌川稳住身形,摇了摇头,目光坚定:“在关外面对胡羯千军万马,末将都未曾后退半步,何况一个藏头露尾的宵小之辈!”
面对刘公公刁钻的长鞭,黑衣人急忙挥剑格挡,然而长鞭这类软兵器对刀剑本就有所克制,只见鞭身一抖,巧妙地避开剑锋,如毒蛇般缠上了他握剑的手腕。
刘公公手腕猛地一沉,长鞭随之震荡,一股暗劲如波浪般沿着鞭。。。。。。
夜色如墨,沉在归语道的尽头。风穿过断碑与残垣,发出低哑的呜咽,仿佛千百个未说完的故事仍在唇边徘徊。那旅人走后不久,雨又落了下来,细细密密地打在石碑上,洗去尘灰,也润开了蓝莲花根下的旧土。
十年过去,春分依旧。
这一年的传灯祭格外盛大。自西北至江南,九十六州县皆有百姓持灯步行,有人提着纸灯笼,有人捧着陶油灯,还有孩童用竹篾扎成星月形状,里头点一豆微光,摇曳如梦。他们不为祈福,也不求神明庇佑,只为走一段路,讲一个人??陈七、阿音、赵五、陆沉……名字越来越多,故事越传越远。
而在归语亭旧址的石坛前,一位年轻女子跪坐良久。她身披粗布斗篷,发髻简单挽起,额角沁着细汗,怀中抱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她不是来祭拜的,而是来“还愿”的。
十年前,她母亲便是那个陷于泥沼的逃荒妇人,靠着陆沉与樵夫们合力拖出马车,才保住性命与腹中骨肉。那一块干饼供在石坛上,成了她一生的起点。她从小听母亲讲述那日清晨的援手之恩,长大后读《守路全录》,一字一句刻进心里。如今她抱着孩子回来,是要让他第一眼看见的,便是这条路、这块碑、这朵蓝莲。
“娘告诉你的话,我记住了。”她轻声说,手指抚过婴儿的脸颊,“谁肯走,谁就能拿。”
忽然,远处传来脚步声。不是一人,而是成群结队,踏着湿泥而来。是一支由各地青年组成的“巡道队”,手持铁铲、麻绳、记事册,肩头绣着一朵蓝莲徽记。他们是民间自发组织的护路义工,每年春分后便沿归语道巡查损毁路段,标记塌方,修补桥基。有人甚至辞去官职,专事此业。
为首的少年见到女子,停下脚步,恭敬行礼:“请问可是林氏之后?我们在《凡人志》抄本中读到你的故事,特地前来寻访。”
女子怔住,随即摇头苦笑:“我不是什么名人之后。我只是……不想让儿子忘了这条路是怎么活下来的。”
少年点头,从怀中取出一本薄册,翻开一页:“这是我们今年整理的新篇目,叫《拾遗录》。里面收录了许多未曾记载的小人物:修桥的老石匠李三,死于雪崩却仍被同伴背回故里安葬;送饭三年不停歇的村妇张氏,临终前只求将骨灰撒在归语道第七站;还有那位蒙面匠人留下的铜牌,已在十二处古道发现复制品……我们想告诉世人,英雄不在庙堂之上,而在泥泞之中。”
女子接过册子,指尖微微颤抖。她忽然问:“你们真的相信,这样走下去,会有改变吗?”
“已经改变了。”少年答得坚定,“去年陇西大水,三十里官道冲毁,朝廷迟迟不拨银两。是我们这群人带头抢修,七日内铺完碎石基底,百姓称它‘蓝莲道’。如今连驿丞都改口说:‘此非官修,乃民筑也。’”
话音未落,天边一道闪电劈开乌云,雷声滚滚而来。众人抬头望去,只见山雾翻涌,竟似有无数身影隐现其间??那是历代守路人留下的足迹,在风雨中悄然浮现。
当夜,他们在石坛旁搭起简易棚屋,围火而坐。女子将婴儿交给同伴照看,自己执笔蘸墨,在一张黄纸上写下母亲当年的经历,并署名“林氏女承志”。她将纸投入身旁一只青铜“传灯箱”中??这种箱子如今遍布全国,形制各异,有的立于寺庙门前,有的藏于书院墙角,还有的沉入江底石窟,以防战火焚毁。
火焰腾起,烧尽旧稿,新字已录于副本之中。
与此同时,在千里之外的长安城南郊,一座废弃作坊静静伫立。门楣上悬一块腐朽木匾,依稀可辨“肃逆司旧坊”五字。这里曾是朝廷监察天下言论之所,如今却被一群流浪工匠占据。他们白日乞食街头,夜晚聚于此地,秘密拓印《守路全录》残卷。
为首者是个独臂老汉,脸上有一道贯穿左眼的疤痕。他原是肃逆司文书吏,因私自抄录《贰拾贰》被判斩监候,后遇大赦流放边关。他在铁脊峡挖矿时结识了最后三位补路人,听闻往事痛哭失声,遂逃回中原,誓要完成一件大事:重铸“宁折不弯”铜牌。
此刻,他正蹲在炉火前,将熔化的铜汁缓缓倒入模具。那模具是他花了三年时间,依据十二枚出土铜牌反向雕刻而成。每一枚铜牌都将送往一位巡道队长手中,作为信物与象征。
“你说……他们会继续传下去吗?”旁边一名少年问道,声音带着怯意。
老汉吹熄炉火,抬眼望向窗外星空:“只要还有人记得阿音在雪夜里背石填壑,只要还有人念着陈七那句‘路为众生而开’,就会有人愿意接过铲子,走进风雨里。”
他顿了顿,低声补充:“我见过陆沉最后一面。他临终前没提功名,也没说仇恨,只问了一句:‘今年的蓝莲开了吗?’”
少年沉默良久,终于开口:“开了。而且比往年更盛。”
老汉笑了,眼角皱纹如刀刻。
翌日清晨,铜牌出炉。十八枚,每枚皆温润厚重,正面刻“宁折不弯”,背面阴文小字:“永和十九年始,薪火相传”。
这些铜牌通过暗线送往各地,有些出现在寺庙香客的布施袋中,有些夹在学子赶考的行囊里,更有甚者,被匿名投递至御史台门口,附纸条一行:“请大人也看一看,什么叫真正的忠臣。”
朝堂震动。
皇帝召集群臣议事,质问为何屡禁不止《守路全录》流传。有大臣怒斥:“此书蛊惑民心,妄议先政,若不严加查禁,恐生叛乱!”
话音刚落,兵部侍郎起身反驳:“可若禁止百姓讲述善行,岂非承认朝廷不如民间有德?况且去年开仓放粮、开放驿道之举,正是因地方官引用书中箴言而促成。若以此为罪,岂非自打耳光?”
殿内一时寂静。
最终,皇帝长叹一声:“罢了。既然万民皆愿读,那就让他们读吧。但须由国子监校订刊行,不得私印。”
圣旨下达当日,民间哗然。许多人冷笑:“官家想收编火种?可惜火已燎原,岂是几页官样文章能扑灭的。”
于是,《守路全录》出现了两个版本:一个是朝廷钦定版,删去了“肃逆司迫害”、“官员贪腐”等敏感内容;另一个则是民间手抄本,依旧完整保留所有真相,且不断增补新篇。
人们私下称之为“真本”与“伪本”。
而在北方边境,一场新的危机正在酝酿。
这一年冬,北狄部落突然集结大军,屯兵于寒脊关外。边报频传,称其意图南下劫掠。朝廷震怒,下令关闭所有关隘,严禁百姓出入,违者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