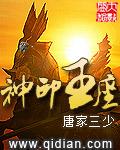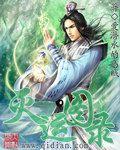秃鹫小说>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豆瓣 > 第84章(第2页)
第84章(第2页)
长安城,似乎从未如现在这般繁华过。建国初的一段日子里,长安城内,未央宫前,时不时有人操着各地方言,辗转前来,要亲自给皇帝献上最新鲜的符命,报上刚发现的祥瑞。
各地官员奏报上来的符命和祥瑞,更是数不胜数。
毕竟王莽一开国就给献符命的人封了侯。封侯,许多官僚和武将一辈子也挣不到,而献符命既不需要有功,也不介意出身,是无本万利的好事。
献符命的人如此之多,连那些爱惜羽毛的人,彼此也会开玩笑说:“独无天帝除书乎?”13意思是:你手里怎么没有天帝给的天书呀?
曾经巍巍赫赫的符命,到此地步,已经和野语村言差不多了。符命所蕴含的神圣和权威也在一天天流失。
五威司命陈崇注意到这个情形,不无忧虑地禀报皇帝说,“这种事情大开奸臣谋取私利之路,淆乱天命,应该断绝其根源。”
王莽颔首,对此他也很厌恶。没当皇帝的时候,符命由民间自发献上是最好的;但如今当了皇帝,符命就不应当由民间来发起,而该由朝廷管控。
皇帝于是安排尚书大夫赵并负责这件事,从此以后,只以五威将帅正式颁布的四十二个符命为准,民间严禁发现新的符命,严禁私献符命,违者下狱。
这是新朝建立后在合法性上遭遇的第一个挑战,而且挑战来源于内部。因为符命被说成上天所降,那么朝廷怎么有资格禁止呢。但不禁止,就会有人利用符命来谋求封侯封官,甚至反对皇帝。
禁令起初还是有效的,那些争先恐后的人群顿时作鸟兽散,想必他们会懊恼为什么不早点献符命吧。
时间一晃,到了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皇帝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行改制,其间,货币改制引起了不小骚乱,与匈奴也因为更换印玺产生了冲突。
面对这些事件,皇帝似乎对他亲手搭建的执政班底并不信任。按理说,大司马、承新公甄邯是三公之首,理应承担更多行政方面的工作,但《汉书》此时已经没有他行政活动的记录。种种迹象表明,皇帝亲自选派中级官员和将军来处理这些事务,可能把三公都晾起来了。
作为政坛老人,甄邯能辨识出皇帝正在疏远帮助他登基的功臣,着手拔擢使用年轻的大臣,眷顾王氏家族的后生。
甄邯大约看得比较开,既已位极人臣,正好告别案牍劳形。甄邯的兄长甄丰就不一样了。早在汉平帝时期,他就已是三公之一的大司空,居摄期间担任太阿右辅,是王莽当时的左膀右臂,常常和王莽商量政事到深夜,人称“夜半客,甄长伯”14,主持吕宽案时牵连构陷不遗余力。但在新朝,他却仅被安排为“四将”之一的更始将军,且与卖饼的王盛、守城门的王兴同列。
表面上看,甄氏家族在新朝很显赫,除了甄邯、甄丰两兄弟,甄丰的儿子甄寻现在是京兆大尹,加官侍中,封茂德侯。不过,甄氏家族内部如果经常走动,理应会表达彼此的不满。特别是甄丰,想起翟义起兵的时候,是他亲自带着兵器在宫中昼夜巡行,保卫王莽,如今换来这种待遇,怎么能不憋一肚子气呢。
王莽登基后,深居省禁,甄邯、甄丰已经不容易见到他了。甄寻担任侍中,还能经常侍从左右。对父亲和叔父的境遇,甄寻也颇觉心寒。他大概从内心里认为,若没有甄氏兄弟的襄助,王莽哪能这么容易登基呢。出于对王莽的熟悉,他发现虽然朝廷已禁止私献符命,但王莽对符命仍然笃信不疑。甄寻于是琢磨了一个法子。
这个法子和当年吕宽、刘宇等人的想法差不多,吕宽想用灾异吓唬王莽,而甄寻想用符命操纵皇帝。
从后来发生的事推测,甄寻并不是一个人琢磨的,而是和刘歆的两个儿子隆威侯刘棻、伐虏侯刘泳,大司空王邑的弟弟、五威将军、掌威侯王奇,以及刘歆的学生、骑都尉、侍中丁隆等合谋商议,这几个人在当时都属于中生代。当然,此事真正的主谋当是愤愤不平的甄丰。
于是此后有一天,甄寻突然向皇帝上奏,说发现一道新的符命。
考虑到禁止私献符命的法令颁布不久,甄寻可能做了解释。这道符命的意思是,当年周朝初建,周公居东,召公居西,两人分陕而治。周、召都是周朝道德高尚的大臣,《诗经》里的“周南、召南”就是从他俩而来。如今,新朝恢复周代圣治,也应分陕而治,由甄丰为右伯,太傅平晏为左伯。
这道符命,大概率是根据公羊学所造,因为《公羊传》里记得很清楚:
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15
《礼记》里也有“周公左,召公右”的说法,所以,甄寻想以这种方式抬高父亲的地位,而且还谦虚了一下,把同样被皇帝挂起来的平晏抬得更高,比照周公,称为左伯;甄丰比照召公,称为右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