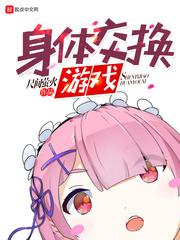秃鹫小说>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 > 第50章(第1页)
第50章(第1页)
但是,刘彻对赵绾、王臧两位昔日宠臣竟没有营救的举动。揣测刘彻内心,可能与申培公师生令他失望有关,这批鲁学的儒生虽然自诩得到孔子真传,但并不符合他的理想。而且外廷也没有几个儒家官员,没有人为赵、王说话。
大概是这个时候,去年出使匈奴的公孙弘回来了,刘彻认为他有辱使命,褫去博士职位,逐回淄川。
4.董仲舒之惑(二)
赵绾等人的倒台,使得明堂、巡狩、历法等儒家制度设计一概停摆,朝廷里没人敢再提。但是,刘彻登基时颁行的举贤良的政令并没有废止,而且几年后(建元五年19)刘彻设置了“五经博士”,这说明皇帝并没有忘记儒学。
博士品秩虽然不高,也没什么权力,却是汉朝的最高学术顾问团,为朝廷设计礼乐制度,时常被皇帝召见询问国家大事、解读祥瑞灾异。以前,汉朝虽然也有儒学博士,比如董仲舒自己,还有去世的申培公,走了的胡毋生,以及被召回来的辕固生,但他们都不是五经博士,换句话说,那时候儒学博士只是太常里众多博士之一。因此,设立五经博士,就意味着博士已经以儒生为主体,儒学融入帝国制度的程度加深了。
董仲舒当上五经博士的第二年春,汉朝有两处重要的宗庙发生火灾,这在当时是很要紧的事。先是二月,辽东郡高皇帝的宗庙起火,接着是四月,高皇帝长陵陵园的寝殿又起火。刘彻十分惊惧,换上素服,并诏令董仲舒奏对。
董仲舒如临大敌,思来想去怎么奏对。火灾这种灾异,他很熟悉,就是阳气太盛引起的。而“阳”所指的不是别人,就是皇帝。
在奏对的草稿中,董仲舒写下:“阳失节,火灾出。”20
最后,他又取出一份新的竹简,备好刀笔,誊写清稿。他考虑再三,不敢写皇帝失节,而是把笔墨花在解释为什么火灾会发生在高皇帝庙这个地点上,以及怎么消除灾异。
奏对送到皇帝手中时,刘彻的素服已经穿了五天,他内心惊惧未消,不敢除服,徐徐展开董仲舒呈上的简册细读,赫然一句话映入眼帘:
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视近臣在国中处旁仄及贵而不正者,忍而诛之。21
原来,董仲舒把火灾归咎于外有不法的诸侯王,内有不安分的近臣,必须将其诛杀。这是间接点出皇帝的责任,但皇帝并没有注意到这层意思,反而觉得,儒学竟然还有如此肃杀的一面,果然博大精深,与当年申培公那句“少说话,多做事”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刘彻,后人常常用“多欲”来形容他,在历代帝王的谱系里他从来不是一位符合儒家口味的君主。他对儒家的喜好,是希望用儒学为他的一切行为蒙上合法、道德、神秘的面纱。董仲舒从一场火灾出发,竟然能够谈及对王侯贵戚的冷酷制裁,这让刘彻嗅到了儒学复杂的味道,儒学的齐学也就进入了他的视野。
三个月后,太皇太后窦氏崩殂。不到一个月,皇帝就以丧事办理得不好为由,将丞相和御史大夫同时罢免。不出所料,原太尉、武安侯田蚡拜相,而曾以五百金贿赂田蚡的韩安国被拜为御史大夫。到了冬十月,已经即位六年的刘彻第一次改元,几个月后,他又下诏举行了汉朝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次贤良对策。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次贤良对策出了两个颇受皇帝瞩目的人,一个是董仲舒,一个是公孙弘22。
公孙弘回来了,齐学的势力增强了,这对董仲舒应是一个好消息。
公孙弘被赶回齐地,本来已经绝了入仕之念,无他,年龄已过花甲矣,他大概有寿则多辱的感触吧。但淄川郡坚持举荐他参加贤良对策,他只好再次西行,跋涉至长安,又来到太常寺。他和董仲舒都知道,此次对策是皇帝真正掌权、大举推行儒学的准备工作,皇帝到底如何看待儒学,如何尊崇儒术,都将在此次对策后见结果。
董仲舒所作的对策就是著名的“天人三策”。后世因为班固在《汉书》里收录了全文,使这三篇奏对极为有名,以至于后人误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已经实现。但司马迁凭着还是董仲舒的学生,在《史记》里对董仲舒的记录却篇幅很短,也没有收录“天人三策”23,可想而知,董仲舒的对策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轰动,而是被后世儒生不断推崇,最终才声誉显赫的。
事实上,“天人三策”也的确没有令皇帝非常满意,皇帝册问的那些问题直白、功利、咄咄逼人。在前两次册问中,皇帝问:“三皇五帝既然道路是对的,怎么最后就走到了桀纣?儒家推崇的复古,到底有没有用?儒家标榜的圣君,为什么尧舜就很闲,垂拱而治;而周公就很忙,连饭都吃不安生?朕现在劝农,为何没有效果?”
皇帝一如既往地急迫,他追问的还是那两个字:治乱。
而且不要务虚,不想听大道理,要听“政治改革”的“解决方案”,不然就来不及了!
可董仲舒偏偏讲的就是大道理,他一方面并不畏惧皇帝,直言“天人感应”的道理,陈说君主必须畏惧天命,自省而行道;另一方面,也不得不回应皇帝的质问:不是尧舜的道不对,是桀纣无德,不是复古没用,是没有真正复古。所以,如今汉朝用的秦法要更化改制。尧舜很闲是因为他们靠禅让得了天下,周公很忙是因为周文、武王靠革命得了天下,形势不同。至于皇帝劝农效果不佳,是因为没有养士,应该从儒生中选拔人才充任到中央和郡国的中层岗位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