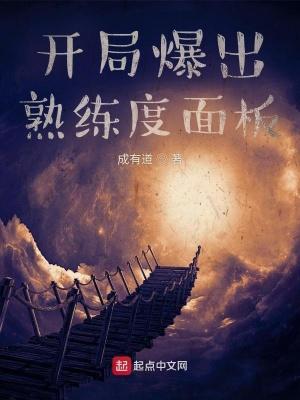秃鹫小说>我在古代办报社 > 营销(第1页)
营销(第1页)
按照孟允抒的吩咐,店内的几个伙计将两块蒙着纸张的木板搬到采闻堂。
孟允抒指挥着他们将木板放到居中的位置:“再往右边挪一点,对。拉开两个木板之间的距离。”
胤朝没有黑板和粉笔,孟允抒就想了这么个办法,找来两块大木板,将白纸蒙在上面,用毛笔在上面写字时注意少蘸些墨,这样就可以实现类似现代社会的教学方式。
她走到采闻堂最后方,打量着两块木板,确认在此处也能看得见上面的文字。
在那两块木板当中,左边那张纸上已经写满了字,从《三字经》的第一页讲起,直至宣纸上写不下为止;另一张则是空白,供她根据课堂内容灵活调整。
排云兴冲冲地从门外快步走来,她身后还跟着两个身着素色衣衫的女子:“孟社长,她们是来参加识字会的。”
孟允抒热情地迎进两人,请她们落了座:“两位娘子请稍候片刻,待巳时一到,我们就开始授课。”
从回城后孟允抒就开始着手准备讲学事宜,她联想到曾经在现代书店见过的“读书会”活动,觉得这是个不错的营销手段,在传播文化的同时也能推销店内的商品。于是,她借鉴这种模式作了初步的计划和安排,对外放出报社要举办“识字会”的消息。
首次识字会将由她主讲,根据课程效果和反响再作调整。
两人向孟允抒道过谢,其中一人腼腆地笑了笑:“我夫君每日都要看报,案上堆满了纸张。我听他说,小报上有诸多奇闻轶事,我心生好奇,却因不识字而无法读懂其中内容。近日我曾听闻黎民报社中要举办识字会,故来洗耳恭听。”
孟允抒没和她们聊上几句,因为在她们之后又陆续来了不少人,孟允抒店内的伙计跑前跑后,忙着招呼来客。他们大多衣着简朴,不少人还穿着破破烂烂的草鞋,打眼一看就是最寻常不过的平民。众人来听课的理由也各不相同,有单纯前来瞧新鲜凑热闹的,有带着孩子来蒙学的,还有像那妇人与从前的排云一样,为了能够读书看报而学习识字的。
很快,采闻堂中就挤满了人,呈现出一派沸反盈天的景象。
当孟允抒再次折返回门口时,发现那里站着一个熟悉,但令她十分意外的身影。
她惊疑地看向陈暄。
“你怎么来了?”
陈暄尴尬地抹了下鼻子,装出一副打量采闻堂的样子:“我听闻你们报社要举办什么识字会,心生好奇,所以来看看。”
他踌躇了一下补充道:“你和许大人为修远申了冤,我感激不尽。你若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就尽管开口。”
“你先进来吧。”孟允抒带陈暄进了门,寻了个空处落脚。她觉得他的表现挺稀奇,忍俊不禁道:“平日你说话总是夹枪带棒的,这会来帮忙,反倒不好意思起来了。”
面对她的调侃,陈暄赶紧岔开话题问道:“这些人都是来参加识字会的?”
孟允抒回头望向满堂的来客,点了点头。
他沉默片刻,而后露出一个释然而苦涩的微笑。
“如此一来,他的心愿也算是实现了。”
孟允抒当然明白陈暄口中的“他”是指谁。
许昭押送柳玉成至刑部之后,陈暄就在第一时间给陈修远的家人写了信,向其告知案件真相,并联合他们写了谅解书,请求刑部官员对柳玉成宽大处理。
陈暄说,因为陈修远的死,他永远不会原谅柳玉成。
但是,他希望这世上能早日多出一位柳先生。
孟允抒看了看院中的那个滴漏,发觉时间差不多了。于是,她站到采闻堂最前方,高声维持纪律:“请诸位安静一下,识字会要开始了。”
她看向采闻堂后方乌泱泱的人头说道:“我们社中没有那么多椅子,辛苦后面的那些兄弟姐妹站着听讲。麻烦个头高的人往后站站,别挡着后面的人。”
除过她这个主讲人外,排云担任此次识字会的助教,还有另外一名伙计作为机动人员,加上陈暄这个志愿者,在几人的合作下,不多时堂内就安静下来。
管理好秩序后,孟允抒继续说道:“感谢诸位莅临黎民报社,参加此次识字会。我们再次承诺,识字会是由报社自发举办,不会向诸位收取任何费用。”
她扫视了一圈屋内的人。男女老少都仰起头,一齐向她投来目光。在这些目光当中,有的是困惑,有的是好奇,还有的是感激。
恍惚之间孟允抒仿佛看到,在他们身后,站着江芷兰,还有柳玉成。
虽然他们的身份、性格、际遇都截然不同,但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词汇。
“这就是‘人’。”
孟允抒指着木板上的第一个字说道。
她拆解着这个字的结构:“‘人’字由一撇一捺组成,它们彼此支撑,互相搀扶,构成了这样简单却和谐的字。”
将第一句话的每个字都单拎出来讲解后,孟允抒让大家齐声朗读一遍。
粗犷与轻柔的声音混在一起,沧桑的语调和着清脆的童声,将这句话拉得很长。